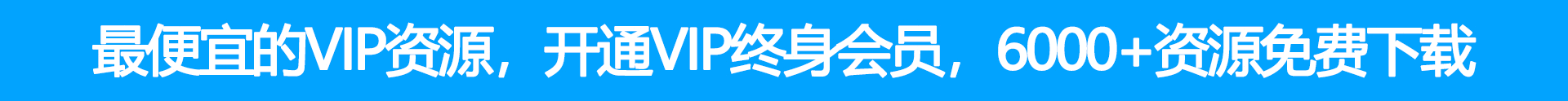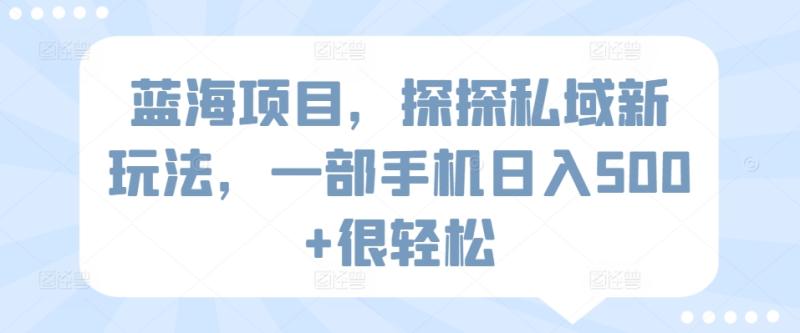![图片[1]-夏目漱石先生去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夕,其经典巨著《文学论》出版-一鸣资源网](https://www.yiming818.com/wp-content/uploads/4ffce04d92a4d6cb21c1494cdfcd6dc1-353.jpg)
夏目漱石
Natsume Sōseki
1867年2月9日-1916年12月9日
日本作家、评论家、英文学者,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他对东西方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他对个人心理精确细微的描写,开启后世私小说风气之先。
明天是日本近代大文豪夏目漱石逝世百年的纪念日。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夏目漱石先生的经典文学理论、文学评论集《文学论》。
在本版《文学论》译者王向远先生所写的译者序言中写道:
该书是作者1903年至1905年在东京大学的讲稿,1907年整理出版,到现在刚好一百年了。一百年,至少经历了三代人,确实是很久了。然而只要读者此前有过《文学概论》、《文学原理》之类的书籍阅读或课程学习的经验,那么读一读《文学论》,就一定会感到惊讶,会觉得没想到夏目漱石是这样论述文学,这样叫人耳目一“新”!
例如全书第一编第一章开门见山地说:
一般而论,文学内容,若要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F+f)。其中,F表示焦点印象或观念,f则表示与F相伴随的情绪。这样一来,上述公式就意味着印象或观念亦即认识因素的F和情绪因素的f,两者之间的结合。
用公式(F+f)来对“什么是文学”这个概念作出定义和解释,大概也是独此一份了。
全书的这些基本结论,如今对于大多数专门的文艺理论研究者而言,已经成为共识或者通识,但即便如此,这部充满文学家敏锐感觉和哲学家睿智与深刻的《文学论》,也仍然给人以新鲜感,仍对我们有相当的启发。
而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体现出的对文学“取‘全义’的视阈,突破了特定思潮流派、特定时代语境的束缚”,“将英国式的文本批评和德国式的逻辑思辨结合”,以及“横跨东西的世界文学视野,运用了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的文学理论观点,让这部鸿篇巨著“在20世纪初年之前的欧洲与日本的同类著述中异军突起、出类拔萃”。
这大概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夏目漱石的《文学论》自1931年张我军先生译本出版之后,迟迟未有新的中文译本。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论》由王向远先生担任翻译。王先生在本版译者序中写到:
在中国,漱石的《文学论》的中文译本由张我军翻译,于1931年在上海出版,周作人写序推荐。虽然现在看来该译本错译、不准确翻译甚多,但对《文学论》在中国的传播是有贡献的。《文学论》中的观点也对中国现代文论有所影响。据方长安先生的《选择·接受·转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一书的研究,成仿吾在1922—1923年间发表的《诗之防御战》等一系列理论批评文章,“对五四运动以来文学中出现的哲学化、概念化和庸俗化的写实倾向,作了批评,提出了自己的救治方案。而如果将他们与夏目漱石的《文学论》相对照,便可发现其诸多立论与《文学论》相同,而这种相同,从基本概念、观点、论述方式等角度看,绝非跨文化语境的巧合,实属直接借用的结果”,并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
翻译方法上,我一如既往坚持“信”或“忠实”是第一,能迻译(直译)的地方尽量迻译,少数不能迻译的地方才释译,而翻译出来的东西则必须是纯正的中文。在此前提下,也尽量总体上保持一些原作的风格,甚至不妨带上一点若隐若现的“日本味”。
今天,在夏目漱石逝世百年纪念日前夕,与大家分享由其本人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从中可以了解一下夏目漱石创作这本文学巨著的来龙去脉。
![]()
《文学论》作者自序
文|夏目漱石
译|王向远
– 声明:如需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想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过程,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被用作大学文学课讲义,现在又缘何公开出版。
我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奉派赴英国留学,当时我正在第五高等学校担任教授职务。得到留学通知时,我并不特别希望出国,同时觉得应该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于是就向校长及教头说出了我的想法。校长和教头答复说:是否有更为合适的人选不是由你来说的,本校已向文部省推荐你,文部省接受推荐予以批准,决定选派你为留学生,若无异议,你最好从命。我虽然没有特别想去留洋的意愿,但也没有固辞的理由,所以只好答应了。
留学通知中要求我去英国研究的科目是英语而非英国文学。为了弄清研究的具体方向和范围,我特意去了文部省,向时任教务局长的上田万年先生请示。先生的答复是:对于学什么并无特别的严格要求,只是希望学习一些回国后可在高中或大学里教授的学科。听到这话,我想虽然要求学习英语,但多少还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变更的余地。就这样,我在同年九月踏上了西行的旅途,于十一月到达了目的地伦敦。
到英国后,首先需要确定留学的学校。留学地点有好几处可供选择,牛津、剑桥均是学术重镇,早有耳闻,正在犹豫时,得到了身在剑桥的友人邀请,于是我前往剑桥观光。
![图片[3]-夏目漱石先生去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夕,其经典巨著《文学论》出版-一鸣资源网](https://www.yiming818.com/wp-content/uploads/4ffce04d92a4d6cb21c1494cdfcd6dc1-354.jpg)
英国留学期间的夏目漱石(冈本一平 绘)
剑桥之行,除拜访友人之外,还邂逅了几名日本青年,他们都是为取得绅士资格,每年花费高达数千元之巨的绅商子弟。我每年从政府得到的学费只有一千八百元,这点钱在这个金钱万能的地方是根本不够用的,没条件像那些绅商子弟那样挥洒自如。不过,在和那些富有的绅商子弟的接触中,我倒没有看见所谓的绅士风度。而我这点钱,即便谢绝一切交际,只是旁听一些必要的课程也很难应付。即便万事小心节俭,努力渡过难关,对于我想要购买的书籍,在归国前恐怕连一卷也买不了。我又想,自己的留学和优哉游哉的绅商之子的留学是不同的。须知英国的绅士是性情优秀的模范人物的集合体,像我这样在东洋度过青年时期的人,若要模仿英国年少绅士的言行举止,就如同骨骼生长已经定型的成年人再想练习舞狮技艺一样,无论怎样佩服,如何崇拜,如何艳羡,即使甘愿忍饿而将三餐缩减为两顿,也依旧无济于事。据说他们上午去听一两个小时的课,午餐后户外运动两三个小时,下午茶的时间相互拜访,晚餐则去学校与众人聚餐。我深知自己无论在金钱、时间还是秉性方面,都没有条件效仿他们绅士的举止,于是就断了长期驻留那里的念头。
我想牛津与剑桥应该是一样的,故而无意前往。我甚至考虑去北方的苏格兰或渡海前往爱尔兰,但这两个地方都不适宜练习英语,于是只好作罢。同时,我意识到只有伦敦是最适宜学习语言的地方,于是就决定在此学习。
伦敦是最适宜学习语言的地方,其理由不言而喻。我当时是这样想的,至今仍然这么认为。然而,我来英国的目的并不单单为了提高语言水平。官命是官命,个人意志是个人意志,在不违背上田局长要求的范围内,我有满足自己意志的自由。在熟练掌握英语的同时从事文学研究,不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同时有一半也是为了服从上田局长的指示。
为避免误解,我还想说一句。我所说的不愿用两年时间只学语言,绝无轻视语言之意,反倒是由于对此极其重视的缘故。学习语言,无论发音、会话也罢,还有写文章也罢,即便只练习其中的一个方面,两年时间也并不算长。更何况学习的内容涉及语言学的各个方面,能够把全部的本事都学到吗?我屈指计算自己的留学时间,考虑如何以自己的菲薄才学在限期内学有所成。再三考虑,最终确信自己难以在预定的期限内如愿以偿。我的研究有一半已经超出了文部省的规定,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诚属迫不得已。
研究文学的话,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学习何种科目呢?这是接下来我要面对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可悲的是,由于浅薄,我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最终都未能解决。我所采取的方法难免是机械的。我首先到大学,听了现代文学史的课程,另外还私下找了一位老师,以方便随时请教问题。
![图片[4]-夏目漱石先生去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夕,其经典巨著《文学论》出版-一鸣资源网](https://www.yiming818.com/wp-content/uploads/4ffce04d92a4d6cb21c1494cdfcd6dc1-355.jpg)
在朝日新闻社工作的夏目漱石(冈本一平 绘)
因为未能产生预想的兴趣和效果,记得大学的课程只听了三个来月就作罢了,但到私塾听课请教问题却延续了一年有余。这期间,我阅读了手头有的与英国文学有关的所有书籍。当然,开始时并没着手搜集论文资料或为回国授课做准备,只不过是尽可能多地随意看了一些书。实际上,我虽然是因英国文学学士的缘故而获选留洋,但却从来不敢自诩精通。毕业后又有几年东西奔波,离文坛的中心越来越远了,忙于个人家事而少有读书机会,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往往只是大略听到过名字,十有六七未曾阅读。对此,在我心中时常引为憾事。利用留学这个机会读尽所有的书是我当时的愿望,此外别无其他想法。如此过了一年之后,再去查看读过哪些书籍,发现没有阅读过的书籍已经很少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意识到,在剩下的一年时间里,若重复以前那样的做法,未免太愚蠢了,于是,我对听课的态度至此不得不发生了变化。
(在此敬告诸位,作为青年学生,风华正茂之际就要立志在某专门领域做出贡献,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广泛涉猎,尽可能多地浏览阅读古今上下数千年的典籍。即便如此,直到白发苍苍之际,恐怕也不能遍览群书。以我为例,至今尚未能够大致了解英国文学的整体,发展的基本情况,也许再过二三十年之后仍然无法做到。)
时日迫近,这种漫无边际的读书方法,除了使当时的我感到茫然自失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促使我脱离以往轨道。我少时好读汉籍,学时虽短,但于冥冥之中也从“左国史汉”里隐约感悟出了文学究竟是什么。我曾以为英国文学亦应如此。若果真如此,我将义无反顾地终生学习文学。我只身投入非流行的英国文学,完全是出于这种幼稚、单纯的理解。读大学的三年时间里,不但为那怎么也学不好的拉丁语和德语所苦,连法语也学得稀里糊涂,重要的专业书籍却几乎挤不出时间来读。就这样,我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获此光荣头衔之时,心中却升起了寂寥之感。
转眼就过了十个春秋,不能说没有学习的时间,唯以学而不透彻为憾。毕业之后,我头脑中不时会有一种被英国文学所欺骗了的不安之念。我怀着这份不安之念,西赴松山,翌年又再往西走到了熊本。在熊本住了几年,此不安之念仍然未释怀时,就来到了伦敦。若在伦敦仍不能消解此种不安之念,那么奉官命远涉重洋,就没有意义了。虽然如此,若希求将过去十年始终未能解开的疑团,在未来一年中解开,即使不能说全无可能,但毕竟希望十分渺茫。
天资愚钝的我,虽专修外国文学,但因学习能力不逮,未能登堂入室,实在遗憾至极。可是,我的学力过去是那样,今后恐怕也再难有所提高。既然学力再难提高,就需要在学力之外涵养品味文学的能力,但最终没能发现解决的办法。回过头来看,我在汉学方面虽然并没有那么深厚的根底,但自信能够充分玩味。我在英语知识方面虽然不能够说深厚,但自认为不劣于汉学。学习用功的程度大致同等,而好恶的差别却如此之大,不能不归于两者的性质不同。换言之,汉学中的所谓文学与英语中的所谓文学,最终是不能划归为同一定义之下的不同种类的东西。
大学毕业数年后,在遥远的伦敦的孤灯之下,我的思考开始转到文学这个问题上了。也许别人视我为幼稚,我自己也觉得幼稚。远渡重洋来到伦敦却想着如此浅显的问题,对于留学生来说应该引以为耻。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我从这一开始就关心这个问题了,我所关注的事情虽是耻辱,但也是事实。我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何谓文学的问题,同时决定利用剩余的一年时间,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阶段。
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将所有的文学书籍都收入箱底。我相信,试图用阅读文学书籍去解决“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如同用血液去清洗血迹一样。我决心从心理方面,搞清文学如何需要,缘何得以生存、发达和衰落。我还要从社会学的方面探明文学如何是必要的,研究文学的存在、兴盛和衰灭。
因为我提出的问题既大又新,相信任何人也不能在一两年间将其解决。因此,我拿出自己的所有时间,尽力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并将可以支配的全部费用购置参考书籍。自从产生这一念想并着手投入这项工作开始,到留学期满为止的六七个月间,是我一生中最为专心致志持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时期,也是汇报书写得不够详尽,而遭到文部省批评的时期。
当时,我尽自己的全部精力阅读所购之书,在认真阅读中详加批注,重要的内容则仔细笔记摘录。开始时的感觉是茫然不着边际,似乎有所领悟之时已是五六个月之后了。我原本不是大学教授,所以没有认识到将此用作讲稿资料的必要性,也就没有急于将其整理成书。当时我的预想是回国后再用十年进行这项研究,待充分完善后再将成果公之于世。
在英国留学期间,我用蝇头小楷手书的笔记本已有五六寸之厚,回国时这些笔记本是我唯一的财产。回国不久,我被委托担任东京大学的英国文学讲师。我并非以此目的留洋,也并非以此目的回国。我自觉得并不具备在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的学力,我的目标是继续进行研究,完成《文学论》的写作,不愿因为授课而妨碍自己实现夙愿,因而意欲推辞。但由于我在留学期间曾在书信中向友人(大塚保治氏)流露出想到东京工作的意愿,在我回国之前友人已将此事安排妥当。我只好不顾自己才疏学浅而任教职。
开课前,我曾为选择授课内容而煞费苦心,我认为对今天研究文学的学生来说,把我的《文学论》讲给他们听,是很有意思的,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我从前在乡下当教师,从那里踏上留学之路,再从海外回到东京,对当时我国文坛的主流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能将自己辛勤研究的成果呈现于接受高等教育、并会左右未来文学走向的青年学子面前,在我是不胜荣幸的。故而决定以此作为授课内容,并期待学生的批评指正。
![图片[5]-夏目漱石先生去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夕,其经典巨著《文学论》出版-一鸣资源网](https://www.yiming818.com/wp-content/uploads/4ffce04d92a4d6cb21c1494cdfcd6dc1-356.jpg)
《文学论》草稿
![图片[6]-夏目漱石先生去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夕,其经典巨著《文学论》出版-一鸣资源网](https://www.yiming818.com/wp-content/uploads/4ffce04d92a4d6cb21c1494cdfcd6dc1-357.jpg)
《文学论》扉页(1907年5月刊行)
遗憾的是,我的《文学论》原本是计划用十年时间完成的大课题,重点是从社会心理学切入,从根本上论述文学的活动力,但还不具备向学生讲授的体系规模。不仅如此,感觉作为文学课的讲义,又有些侧重于理论,偏离了纯文学的领域。这样我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将已经搜集尚未来得及整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某种程度的组织框架;二是将略已成系统的理论论述,尽可能联系纯文学作品加以讲解。
在身心健康及可用时间皆不许可的条件下,我认为两者兼顾绝无可能。然而计划如何加以实现呢?书中的内容本身将回答这个问题。授课时间是每星期三个小时,从明治三十六年九月至明治三十八年六月,前后持续两个学年。当时的授课,似乎没有像我所预期的那样吸引学生。
我原计划第三学年继续教授这门课程,但受种种事情妨碍未能实现。本打算将讲述中发现的不足之处加以重写,竟也未能实现。此后将此书稿弃之箱底约有两年,此次应书肆之邀,公诸于世。
应允出版之后,为身边琐事所困,连亲自誊清旧稿的时间都没有。不得已,委托友人中川芳太郎氏代为编辑目录、区分章节以及它的整理工作。中川具有广博的学识和笃实的品质,也曾听过本书部分内容的讲述,是处理此事的最佳人选。我非常感激他的帮助,只要此书还存在于世上,他的名字就不会被忘记。如果没有他的真诚帮助,这本书的出版就不可能如此顺利。有朝一日,中川若成名于文坛,这本书或许会因他的名字而加深在世人中的印象。
如上所述,此书是我辛勤研究、精心结撰的成果。但因十年的写作计划缩短为两年(说是两年,除去出版前修订所花费的时间,实际上仅仅用了两个夏天),又未能像喜欢纯文学的学生所期待的那样调整原来的结构,至今仍不免是个未定稿或未成品。然而学界事务繁忙,我本人又比别人更忙。本应再弥补不足、纠正差错、扩充内容之后再付梓出版,但是我的生存状况若不彻底改变,即使穷尽一生的岁月也难以看到此书问世,这就是我之所以将这个未定稿交付出版的缘由。
将未定稿出版,并非为了用于现在学生的授课,也不是要让人知道文学为何物,而是希望本书的读者在掩卷之余,能够思考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疑问。若有人能在本书所提问题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进两步,探得文学径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学问的殿堂的建造绝非一朝之事,也绝非一人之事,我愿为此奉献微薄之力,尽一份义务。
在伦敦居住、生活的两年是极为不愉快的两年。我在英国绅士之间,犹如一匹与狼群为伍的尨犬,终日郁郁寡欢。据说伦敦人口有五百多万,自己当时的状态犹如掺和进五百万滴油珠中的一滴水,勉勉强强苟且维系着朝不保夕的生命。假若一滴墨汁掉落在洗得十分干净的白衬衫上面,衬衫主人的心情定然不会愉快。我就如同那滴招人厌烦的墨汁,犹如乞丐一般徘徊在伦敦的西斯敏斯特大街上,两年间吞吐了这个大都会几千立方尺人工造成的充满煤烟污染的浑浊空气,为此而感到深深愧欠于英国的绅士们。我在此敬告一向被自己视为绅士模范的英国人:我并非是怀着个人的好奇心进入伦敦的,而是受到比个人意志更大意志的支配,不得不在你们面包的恩泽之下度过那段岁月。两年后留学期满回国,我的心情犹如春天到来、大雁北归一般。遗憾的是,不仅客居留学期间我没能做到以你们为楷模,万事顺应你们之意,而且时至今日作为“东洋的竖子”仍然未能成为你们所期望的那种模范人物。然而,我是奉官命前往的,并非是自己要求前去的。若依我自己的主观意志而言,我当终生一步也不踏上英国的土地。因此,承蒙尔等关照的我,绝不会期许再次得到尔等的关照了。我对不能再有感谢尔等厚意的机会,而甚感遗憾。
回国已逾三年,这又是不愉快的三年岁月。然而,我是日本的臣民,不能以不愉快为由而离去。拥有日本臣民的荣耀和权利的我,生存在五千万人之中,至少有着能够支配五千万分之一的荣耀和权利。当这份荣耀和权利被消减到五千万分之一以下时,我也无法否定自己的存在,也不能采取离开本国的行动,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努力使其恢复至五千万分之一。这并非我的意志,这是我意志之上的意志。我意志之上的意志令我的意志无可奈何。我意志之上的意志命令我,为支持作为日本臣民的荣耀和权利,必须避免一切不愉快。
将著作者的心情毫不掩饰地写在学术著作的自序中,似乎有欠妥当。然而,若想一想这本学术著作是在何等不愉快中萌芽,在何等不愉快中成形,又在何等不愉快之中讲授,最后又是在何等不愉快之中出版的,那么,即便与其他学者的著作相比,拙作也许不足为重,但对我个人而言,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已经深感满足,读者多少也会感到理解同情了。
英国人把我视为神经衰弱。当时有位日本人曾给国内写信,声言我已发疯。贤士所言,当无虚假。余不敏,未能对这些人等表达谢意,深感遗憾。
写《我是猫》时候的夏目漱石(冈本一平 绘)
回国后,我依然被说成是神经衰弱兼狂人,似乎连一些亲属也都认同了上述说法。既然连亲属都表示认同,我本人也自知没有辩解的余地。正是因为神经衰弱与狂人,我写出了《我是猫》,出版了《漾虚集》,《鹑笼》也得以面世。这么一想,我坚信我应该感谢这神经衰弱症和我的癫狂。
只要我的生存状况不发生变化,我的神经衰弱和癫狂将与生命永存。既然永远存在,就有出版更多《我是猫》、更多《漾虚集》、更多《鹑笼》的希望。我祈求这神经衰弱与癫狂永远伴随我。
这神经衰弱和癫狂不容置疑地驱动我进入创作状态,不知今后是否还会有摆弄《文学论》这种有闲文字的余裕。惟其如此,就应写一篇文章作为我曾染指这类著作的一个纪念。即便此书没什么价值,但对作者而言,毕竟是给印刷厂添了麻烦。
特记此书由来如上,是为序。
夏目金之助(夏目漱石的原名)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十一月
(完)
相关图书推荐
《文学论》
[日] 夏目漱石|著
王向远|译
《文学论》是夏目漱石在东京大学的讲义,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从心理美学、读者接受角度写成的文学原理著作,既有文本特色,又具世界性的广泛影响。《文学论》从社会心理学、美学 出发,认为文学的内容由观念、理智、印象等 “认识” 方面的要素(漱石用 F 来表示)与情绪的要素(漱 石用 f 来表示)两部分构成,并创造了 F+f 的文学公式,由此展开了他的文学观。
如您对这本《文学论》感兴趣,
试试长按下图二维码或戳文末“阅读原文”吧
说明:
昨天推送的关于谷崎润一郎的文章《如果没有我崇拜的高贵女性,我就无法如愿地创作》,摘自岛内景二所写的《谷崎润一郎评传》。因为与编辑部沟通失误,将本文的译者林青华老师误标为了作者。特此说明,并向广大读者以及林青华老师致以歉意。
上海译文
文学|社科|学术
名家|名作|名译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stphbooks”添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