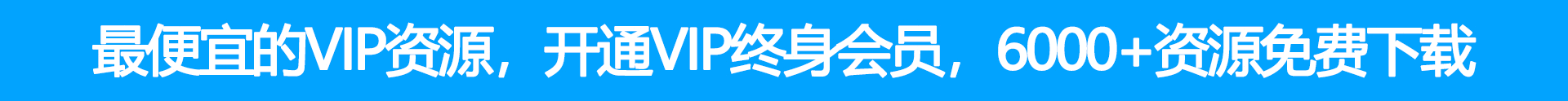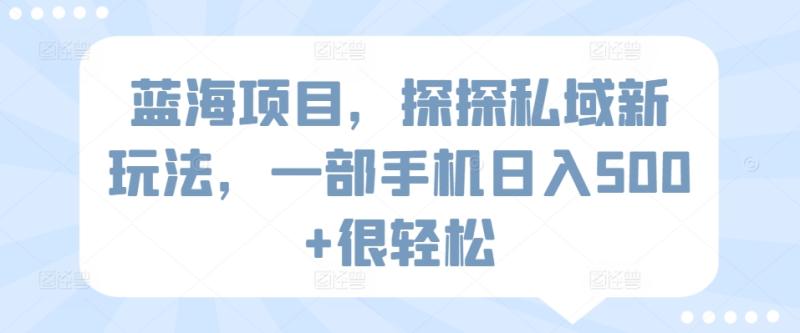写在前面的话
1991年10月,“盖尔号”(Andrea Gail)商用剑渔船从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的港口出海捕鱼,返程时遭遇了“格蕾丝”飓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20英里,海浪汹涌到地球上几乎没有人见过的高度。经过一番挣扎和营救,6名船员不幸全部遇难。1997年,塞巴斯蒂安·荣格将该故事写成了小说,命名《完美风暴》(The Perfect Storm)。2000年,沃尔夫冈·彼得森执导、华纳兄弟公司投资的同名电影上线,广受好评,全球票房高达3.3亿美元。现在,“完美风暴”一词也常被用以形容“金融海啸”。本文回顾2020年2-3月大流行爆发后美国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它完全符合一场“完美风暴”的前奏,但为何戛然而止?
截止到2020年3月初,国内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本土新增确诊降到了个位数),而美国疫情的扩散才刚刚开始。新冠大流行是百年一遇的外生冲击,基本传染数远高于其它传染病,早期除了社交隔离之外没有其它有效的防控办法。
恐慌情绪和悲观预期的发酵刺激了对安全资产的需求,触发了一场流动性危机。大危机的记忆还是崭新的,市场担心流动性危机演变为偿付危机,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大面积破产,就业岗位大量消失,全球经济又将滑向深度衰退。
如果将局部的流动性危机到系统性金融危机,再到深度经济危机的演变称为“完美风暴”,那2020年3月的美国金融市场就是一场典型的完美风暴的序曲,后续的全面金融危机和深度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兑现,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第一时间作出了响应,在“第一束火焰”蔓延之前就将其扑灭了。这也是大危机的深刻教训。
一次典型的流动性危机
用一句话简单概括流动性危机的特征事实就是:流动性溢价快速上升,具体表现为风险资产价格的急跌和安全资产价格的急升——既体现不同类型的资产之间,也体现在同类资产内部。比如在风险资产内部,信用评级越低的企业债,利差上升越大;估值越高的股票回撤越大;再比如安全资产,以国债为例,期限越短,流动性越高,在出现流动性冲击时也更受投资者青睐,所以往往会出现长、短期国债利率大幅背离的情况——短期国债利率下行,长期国债利率上行。
这些都反映的是投资者“追逐现金”(dash for cash)的交易行为。交易员和对冲基金需要现金来偿还短期债务或满足追加保证金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包括投资于流动性相对较差的公司债券的共同基金——需要现金来应付恐慌的投资者的撤资。保险公司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希望持有更多现金(而不是股票和债券),以降低整体风险敞口。外国政府和央行需要美元在外汇市场上支撑本国货币,或向本国银行放贷。
2020年2月底到3月底,美国金融市场的运行几乎符合流动性危机的所有设定。美股从2月下旬开始下跌,从3月开始加速,10天内4次触发熔断机制(图1)。从2月19日的高点到3月23日的低点,标普500指数累计回撤幅度高达34%,急跌的速度超过了1929年大崩盘和1987年恐慌。标普500波动率指数(VIX,又称“恐慌指数”)飙升至82.69,超过了大危机时期的记录(80.86)。另一方面,大流行期间,美股收复失地的速度也是史上最快的,标普500指数仅用了127个交易日(2020年8月18日)就回到了前期高点。
1987年恐慌美股两个月内回撤了36%,耗时22个月回到前期高点;2001年和2008年的最大回撤分别为38%和54%,均耗时48个月才创新高。大萧条期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直到1932年6月(前期高点为1929年9月)才触底反弹,跌幅高达89%,收复失地还要到1954年底。
大危机和大流行期间的两次流动性危机既有共性,又有区别。两者都符合上文所概括的特征事实(图2-5)。最大的区别是,大流行期间的流动性冲击是一次性的,而大危机时期则持续发生。另一显著的不同之处是,大流行期间隔夜LIBOR利率并未大幅上升,反映全球美元流动性明显改善。这与央行之间货币互换的常态化和扩大化有关。
大危机时期,美联储同14家央行开展了货币互换(包括4个新兴市场的央行),缓解了海外美元流动性压力,间接减轻了海外投资者抛售美元资产的压力。大危机之后,美联储常态化了其中5家发达国家央行的货币互换。2020年3月9日,又重启了另外9家。
截止到4月底,通过货币互换,美联储共计提供了4,000亿美元的流动性。此外,美联储还设立了一项特殊的回购工具,允许未参与货币互换的外国当局以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品借入美元,而不必在市场上直接出售这些证券。美联储还明确表示,只要是必要的,该工具就会一直存在。
但这并不能说明大流行期间没有出现美元荒。美元流动性也是分层的,不同市场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如果以货币互换基差(currency swap basis)或泰德(TED)利差来衡量,美元短缺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美元指数快速上升也是一个例证。从3月9日到3月底,美元相对于日元的最大涨幅为9%,相对于瑞郎的最大涨幅为7%,而澳元和新西兰元相对于美元的最大跌幅约为13%。
并非每一次流动性危机都会出现长、短期国债利率背离的情况(图4)。例如大危机期间,在巴黎银行冲击、贝尔斯登事件和雷曼时刻三个关键时间点,长短期国债收益率都是下降的,只是短期利率的降幅更大。但在2020年3月10-18日,长、短期国债利率出现了背离。10年期国债利率在3月9日下降到0.54%后迅速反弹到了1.18%,而1个月期国库券利率则从相同的位置下降到零。这与对冲基金的交易策略有关。
采用多空策略的对冲基金通过质押式回购为现券的多头头寸加杠杆,同时出售期限匹配的期货合约,实现风险对冲,赚取微小的利差。由于现券质押的折扣(haircut)为1%,故投资者可以获得100倍杠杆。收益率也因此被放大100倍。但在流动性危机期间,利率的波动率和期货合约的保证金要求都会上升,尤其是长期美债合约。由于期货市场的流动性加剧恶化,期货隐含收益率下跌得比现券收益率更快,期货空头出现亏损后就会触发“追加保证金通知”(margin call),迫使投资者出售现券的多头头寸,导致10年期国债价格下跌,利率上行。
票据和债券是股票之外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工具。通过票据利差(图5)和债券利差(图6)能清晰地分辨出流动性冲击的时间和强度。以票据利差为例,在大危机期间,不同信用级别的非金融企业票据利差在重要时间节点都出现了脉冲式地上升,其中,A2/P2级信用利差在雷曼破产后升值6%,远高于前期高点,一直到2008年底都在5%-6%之间高位震荡,走势与AA级信用利差有较大区别。
2020年3月底,票据利差也大幅上升,水平相当于2007年8月的“巴黎银行冲击”,到6月初回归正常水平。企业债利差(经期权调整后)的情形类似。
相比新冠病毒,金融市场恐慌情绪的扩散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防疫与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道理是类似的。如同外在的干预手段可以改变疫情扩散的轨迹一样,“有形之手”也能扭转投资者恐慌情绪的传播。
另外,《自然》杂志(Nature)的研究还表明,相比防控措施的严格程度而言,经济损失对封锁时间的长短更加敏感——更早、更严格和更短的封锁也是最经济的。所以,尽早防控,走在病毒扩散曲线的前面是关键。这正好对应着“灭火”的重要原则:第一时间响应。这同样也是损失最小的方式。
不一样的金融周期
金融周期(financial cycle)是经济衰退的先行指标,金融周期的高位拐点对接下来的经济衰退有比较好的指示作用。这是因为,金融周期的本质就是信用周期,它与房地产周期密切相关,因为房地产是信用创造的“基石”,是信用顺周期性的“根源”。
金融周期由升转降意味着信用的收缩和去杠杆,也将伴随着房价的下跌和住宅投资的收缩,进而导致经济衰退。这是大危机后美国经济停滞的一个解释,与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的情形相似。大危机之前,美国金融周期首先出现了高位转折点,但大流行冲击发生在新一轮金融周期上升的中段。
这也是美国经济再次陷入长期衰退的可能性较低的一个原因,因为经验上,如果只是股市崩溃,在《债务危机》中,达利欧(R. Dalio)描述了2007-2011年美国债务危机的演化,认为大危机是非常典型的房地产泡沫,特征包括:风险资产价格大幅偏离合理估值区间;市场普遍预期价格会继续上涨;购房者利用高杠杆融资买入;买家提早买入,以获取价格上涨的投机性收益;新买家持续涌入;货币与信用的宽松;2020年初大流行冲击发生时明显不一样,因为房地产市场还很健康。综合而言,虽然美国房价已经超过前期高点,但房地产市场出现崩盘的概率较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虽然房价已经突破前期高点,但并未出现持续性暴涨的情形。2012年1季度开始,房地美房价指数开始反弹,2013年8月最高时同比增长10%,2014年底至今平均增速为5%,与名义GDP增速保持一致;
•过去10年,美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在持续下降,家庭净储蓄率升至8%的高位,与1990年代初期持平;
•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总额与前期高点持平,占信贷总量的比例从高位的25%一路下行至目前的16%,新增住房抵押贷款占比已降至20%-30%的区间,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比例一度超过80%;
•房贷违约率方面,总体断供比率、优先级和次级新增断供比例均位于过去十年低点;
•居民当期抵押贷款还款额占总体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降至1980年以来的历史低位,2019年3季度为4.12%,较2017年底降了3个百分点。居民和非营利机构的债务利息和摊销负担(DSR)也一直在下行,2007年底为11.5%,目前已经降至7.8%;
•2009年以来,出租房空置率和房屋空置率均处于下降区间,前者已降至6.4%,后者降至1.4%,与20世纪80年代末持平;
从后危机时代美国实体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图6,左图),直到大流行之前,居民部门都在去杠杆。企业部门直到2012年2季度之前都在去杠杆,杠杆率上升最明显的是政府部门,但主要出现在2013年之前,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同步——正是因为企业部门开始加杠杆了,政府才能抽身而出。居民快速加杠杆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但这次不一样。
大危机以来,美国居民(和非盈利机构)部门资产负债率从接近20%的峰值以较快的速度下降到了2018年底的13.1%,债务杠杆率(总债务/GDP)已从高位的98%降至大流行之前的75%,原因是分子和分母双管齐下,分子的债务增速放缓,分母不仅有储蓄存款的增加,还有十年牛市带来的净资产的增加。
在居民部门总资产中,非金融资产中的房地产占比约26%,金融资产占比约70%,其中,约45%为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保险和养老金等占比34%)。本次金融崩溃必然导致居民部门资产负债率的提升。30%的下跌幅度意味着4万亿美元的净资产损失,这将推升资产负债率至13.5%。
所以,短期内,只要股市下跌的次生风险可控,居民资产负债表的衰退的风险也是可控的。
非金融企业部门存在隐忧。在大流行之前,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经超过了大危机前夕的高点(72%)。2015-2018年,美国企业的利润增速在不断下降,同比增速在2010年就出现了高点(24.98%),而后波动下行,在2015年和2018年还出现了负增长,其中,2018年为-3.26%。
两者的合力使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偿债率(debt service ratio)从2013年底触底(36.4%)后开始迅速快速攀升,2019年3季度升值42.7%,较2008年6月的前期高点仅差1.6个百分点。这说明,企业是债务负担较大的部门。这也就可以理解美联为什么要并重启商业票据流动性工具(CPFF)了。
面对2020年3月的深度衰退,还有一个值得乐观的因素是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更加稳健。伯南克称之为“一线希望”(a silver lining)。后危机时代,美国持续加强金融监管,在实施《巴塞尔Ⅲ》上也更加积极。存款机构的各项稳定性指标——流动性比率和资本充足率明显上升。
考虑到当时所面临的极端不确定性,美联储依然启动了针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支持工具,如放松贴现窗口贷款的条件,鼓励金融机构借款。宏观审慎要求有系统思维,在面临流动性危机时,纾困措施不能像“打地鼠”游戏一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多管齐下,这样才能走在恐慌曲线的前面。轻描淡写地说句“悲观者正确,乐观者胜利”是容易的。
因为,历史记载和人的记忆都存在“幸存者偏差”。如果说另一场大萧条本可能发生,应归功于谁?毋庸置疑,美联储可占一席之地。虽然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将来爆发了某种形式的危机,如美股泡沫破裂,或由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震荡,归罪美联储的声音也不会缺席。防患于未然是艰难的,成效也难以评估。货币政策当局总是希望在降低事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事后的道德风险。
历史的天秤正在偏向前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三位“灭火队长”得到的教训是,“在一场载入史册的危机中,当务之急始终是结束危机,尽管这可能会造成一些道德风险,存在鼓励未来无原则冒险的缺陷。”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的破产宣告次贷危机全面升级,美联储(和美国联邦政府)展示出了“行动的勇气”,迅速国有化了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还向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了85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
通过一系列“信用宽松”(credit easing)和“量化宽松”(QE)政策,美联储向货币与金融市场投放了大量流动特性,逐渐平复了市场的恐慌情绪,美国经济也从2009年中开始复苏。伯南克从“大萧条”的历史中深刻认识到:“美联储在信贷紧缩期间对通货膨胀和道德风险的执迷已经导致了一场大萧条,他并不打算重现这一幕”。
十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时,三位亲历者出版了一本名叫《灭火》的书,以期美联储能够在未来的危机中更果断,也希望国会授予美联储更大的自主权。他们认为,如果在发现“干燥的火种”或“第一束火焰”时就行动,2008年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火灾终将到来”,美联储的职责是发现火种,并在火势蔓延之前将其扑灭,因为一旦失控,美联储需要做的更多,萧条持续的时间越长。
快速行动的目的恰恰是少行动。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美联储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时行动更迅速——3月3日降低联邦基准利率50bp,3月15日降100bp至零利率,并立即开始实施QE,出台各种流动性管理工具,如扩大隔夜回购操作规模,重启1个月和3个月期限的回购操作。“灭火”已经成为主流观念。
非常规货币政策已经成为21世纪美联储的行动范式,直到下一场危机将其推翻。
(本文作者邵宇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系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