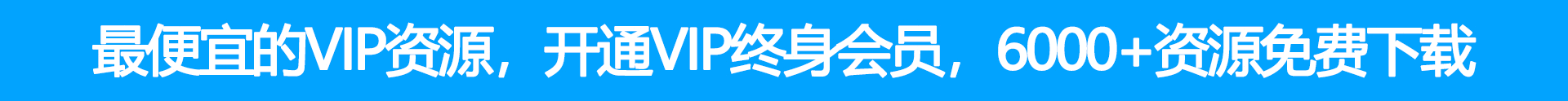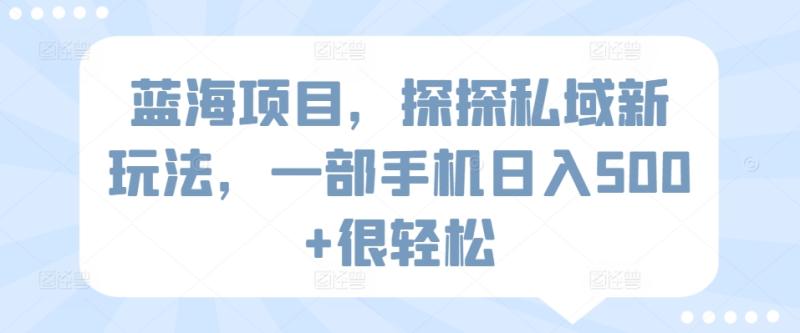走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除了游客之外,最多的外来者就是随处可见坐在路旁身着黑色头巾和罩袍的穆斯林妇女和孩子。
众所周知,土耳其虽然是一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但是这里的穆斯林在着装方面比中东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更开放。所以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学校,都可以见到穿着短裤和人字拖的男人和身着短袖裙子不戴头巾的女人,而在更为传统的阿拉伯国家是天方夜谭的。
所以在伊斯坦布尔的街边,如果迎面走来的是背着名包、身着黑色头巾和罩袍的阿拉伯女性,那么她们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富裕的海湾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游客。
而那些眼神落魄、在街边牵着孩子乞讨的着装传统的阿拉伯妇女大部分则是来自于叙利亚的难民。令我惊讶的是,虽然土耳其人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同信逊尼伊斯兰教,名义上都是穆斯林兄弟,但是土耳其人对这些难民的态度却是几乎一致的疏远和不待见。
这也激发了我对土耳其难民现状和其对外族态度的探源。
一、土耳其难民现状是怎样的?
据统计,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人数接近欧洲的两倍,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有近五百万人跨越边境来到土耳其,其中的两百多万人不堪生活在设施简陋的难民营,不惜向支付当地蛇头巨额偷渡费,以土耳其为跳板冒着生命危险横渡地中海登陆希腊前往西欧。
当地朋友告诉我,这些费用通常动辄即达到一人1500到2000美金。而且蛇头们为了利益最大化,经常用年久失修的救生艇超载运送偷渡客,导致海难不断,五年来已经有四万余人葬身于海底。因为高昂的费用,那些三百多万无法支付偷渡费的难民便选择留在了土耳其。这些叙利亚难民有些居住在土耳其政府和联合国提供的难民营内,有些生活在土耳其各大城市的角落,男人作为非法劳工为当地雇主打工、女人则带着孩子在路旁乞讨。

据统计,由于从叙利亚出走的难民占了整个叙利亚人口的近二分之一,这些难民的原本身份大都属于社会的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所以他们的职业种类也就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在街边面包店打工的叙利亚中年男人也许曾经是公司白领,而在清真寺旁乞讨的叙利亚年轻女子也许曾经是小学老师。
多远化的人口组成让土耳其政府很难为难民们统一定性,也给当地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加剧了社会各派的对立。
一个月前,《土耳其日报》用头条报道了总统埃尔多安对待难民的新政策:埃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当下的执政党)提议为所有难民提供合法劳工证,并对其中长期表现优异的人才提供土耳其国籍。
提议一出,土耳其国内上下一片哗然。土耳其的各个在野党,包括凯末尔所建立的人民共和党均发表言论,强烈抨击埃尔多安的新政策。人民共和党发言人认为总统埃尔多安此举是为了扩大正发党的选民数量,有非法影响来年大选之嫌。
他们认为,合法化难民甚至给予他们国籍会令难民与境内的恐怖分子更加难以分辨,从而加重土耳其当下日渐严峻的安全威胁。埃尔多安的发言人则反驳人民共和党的观点,认为合法化难民是当下叙利亚和谈毫无起色情况之下使难民们正面融入土耳其社会的唯一的解决方案,也是对土耳其滞缓的经济发展的强心剂。两党相争,各自的理由都有其合理之处,而这些对待难民不同的角度也反映了土耳其当下社会对立的现状。
二、民族主义情绪是土耳其接收难民的最后一坎?
其实土耳其从建国以来就不是一个欢迎外来移民的国家。与对文化民族包容的奥斯曼帝国不同,土耳其在凯末尔建国以来一直以民族主义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从19世纪初希腊和埃及相继从奥斯曼帝国独立之后,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浪潮成为了压垮六百年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20世纪初的巴尔干独立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已经名存实亡。曾经一度兵临维也纳城下、疆域横跨亚欧非三个大陆的世界强国,只剩下了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的领土。

此时,一群奥斯曼帝国的年轻贵族军官们决定改变这一窘境。于是他们组成了联合进步党(现代俗称「青年土耳其人」),用军事要挟罢免了奥斯曼君王,开始了他们救国的改革之路(凯末尔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些年轻的军官们为了增强社会凝聚力,决定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建立一套以民族经济和社会体系为框架的国家体制,尽其所能地保存奥斯曼帝国剩余的领土。由于当时还没有「土耳其人」这个概念,「土耳其人」这个词在那时也只是对帝国中部那些没受过教育的农民们的蔑称,于是他们便选择了「奥斯曼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把前奥斯曼领土中的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笼统地分为「奥斯曼人」和「非奥斯曼人」。
而一个从多元的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需要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核心民族」,所以必然要同化所有别的民族,以牺牲其它民族认知的地位为代价来提升核心民族的地位 。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中国,每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该民族「净化」的过程,而这个走到最极端便是我们俗知的法西斯民族主义。
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这些奥斯曼的贵族军官们为了凝聚现有的帝国领土而把一切脱离或即将脱离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定义为奥斯曼的敌人。这些则包括了小亚细亚半岛以西的希腊人、以东南的阿拉伯人、以东的亚美尼亚人等对奥斯曼帝国「不忠诚」的民族(牺牲了150万人的亚美尼亚种族大清洗便是当时的产物)。当时中东地区已经被英国和法国扶持的政权所控制,北非地区埃及等国也相继脱离了奥斯曼帝国而自治,于是便有了后来土耳其人对中东北非地区阿拉伯人的民族歧视,尽管他们大多数同样信奉着逊尼伊斯兰教。
在土耳其建国后,当年在联合进步党中的基层军官、「国父」凯末尔继续践行并深化了这一民族政策。在他的指引下,土耳其与希腊进行了人类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交换,有200多万世代居住在小亚细亚的希腊族人被遣送到希腊,同时200多万当年被奥斯曼君王从西欧接纳并安置在地中海沿海地区的穆斯林被遣送至土耳其。
这次为期近五年的人口交换加深了土耳其的穆斯林对外族的不信任,也增强了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国内的地位。至此,在土耳其的穆斯林终于成了土耳其人口的绝大多数,凯末尔也完成了其前辈们对土耳其民族化的期望。而国家的民族化和人口的单一化意味着不同形式的排外,这也让土耳其骨子里成了一个对外充满了不信任的国家。
虽然近十年来总统埃尔多安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并推动入欧进程,寄希望于把伊斯坦布尔打造成曾经奥斯曼帝国时的世界之都,但是土耳其八十余年来根深蒂固的国家民族主义将会是其国际化道路上最难跨越的一坎。这段历史也可以大致解释今日的土耳其政府和国民在接纳阿拉伯世界的叙利亚难民时刻意疏远并歧视的态度。
三、接纳难民的利与弊:土耳其的叙利亚人何去何从?
在我看来,从社会和心理层面上接纳这数百万难民将是土耳其未来唯一的道路,而完成这一目标需要总统埃尔多安从政策上弱化土耳其当下主要以民族与宗教而双重定义的国民自我认知,并转向由主要以宗教而定义的国民自我认知。
首先需要达成共识的是,若无限期搁置土耳其国内的难民地位问题,那么这不仅会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而且会使土耳其当今每况愈下的社会安全形势雪上加霜。由于阿拉伯人有史以来的鼓励生育的传统,土耳其国内的难民数量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达到指数式的自然增长,可能会达到四百甚至五百万。如果不给予难民合法的工作权,许多难民只能继续极低收入的非法打工而不能进入正式的工作市场,在消耗社会资源的同时不会产生相应的对社会资源的贡献。难民中失业人数也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许多在土耳其出生的叙利亚儿童不能接受正常教育,在长大成年后必将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影响。
但是反之如果土耳其成功地使难民融入了社会,让有技能有专长的人才发挥他们的优势,这将很有可能会给土耳其带来可观的经济增长(移民和合法劳工的增加对社会经济是一针强心剂,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人口对城市经济的贡献以及二十世纪中后期土耳其移民对欧洲重建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叙利亚人从难民向移民的转变将会是土耳其历史上一个天赐良机。不仅经济会增长,而且他们成功的融入将会培养一批热爱国家的良好公民,在政治上也将会成为埃尔多安强有力的支持者,成为其可观的政治遗产。
当然,我们要意识到使难民全盘融入绝不会只带来好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八十多年的民族主义教育让土耳其人的民族观根深蒂固。对民族意识极强的大部分土耳其人来说,难民的融入将会使他们对土耳其的认知和对政府的信任产生巨大的改变,并使他们的工作机会受到威胁。
即便政府通过法案合法化叙利亚难民,这必将会在社会中产生巨大的波澜,并有可能会使政策上的努力功亏一篑。从历史角度上来说,合法化叙利亚难民也将推翻1933年凯末尔的「安置法案」( 限制阿拉伯人和其它非突厥族的穆斯林向土耳其国内的移民并将其定义为二等公民),为土耳其人引以为豪的国家民族主义历史画上句号。
从意识形态角度上来说,因为叙利亚的阿拉伯穆斯林相对于土耳其的穆斯林来说更为传统,所以合法化甚至公民化这些传统派穆斯林的前景与凯末尔的世俗化社会构想是决然对立的,该新政策的实施也将意味着凯末尔主义的历史终结。而在民族主义者仍是土耳其民主社会一股强势力量的当下,埃尔多安政府仍然需要民族主义者们的广泛支持才能得以继续执政。土耳其政府在当下国内的民主政治环境中若决心要合法化难民地位必然要经历长期的与凯末尔主义者和其它反对党的斗争。
四、埃尔多安该如何决定?
如果埃尔多安下决心将难民地位合法化,那么他如何才能成功战胜国内的民族主义党派并使叙利亚人顺利融入呢?
在当前移民政策妥协难以用民主的方式达到的境况之下,集中埃尔多安的行政立法权是一个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制定政策的途径。而2016年7月的政变未遂则给了埃尔多安实现这一目标以天赐良机:政变之后通过对政府各部门的清洗,埃尔多安加强了对政府政策制定权的控制,也迈向了改造凯末尔国家民族主义的第一步。(而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埃尔多安的集权必然会导致民主环境的恶化,削弱言论自由及其它公民权利。本文主要以实际政策来分析叙利亚难民在土耳其融入的可行性问题,对于土耳其民主政治上取舍不做讨论。)
在埃尔多安巩固了自己的绝对权力之后,他便可以继续无阻力地推行社会伊斯兰化的目标。在我看来,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伊斯兰化并不像某些媒体描述的是一件坏事。
首先,伊斯兰化的实质是让伊斯兰教,这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土耳其人都信奉的宗教,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目的并非是要成立一个伊朗式的政教合一的政府(在目前的环境下,土耳其在北约和欧盟晋升国的身份和其国内世俗化的历史使其实施政教合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通过开展宗教和文化教育,大部分世俗化的穆斯林国民可以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以史为鉴对国家的未来进行客观实际的展望。 从政治上来说,土耳其的伊斯兰化只是社会的表象,对法律和行政不会有影响,正所谓伊斯兰化不意味着一定不民主(如2013年之前的埃尔多安政府),世俗化也不意味着一定民主(如1980年政变后的凯末尔派军政府)。
再者,推行社会伊斯兰化更能弱化土耳其人心中的民族主义诉求,让对博大宗教信仰的认知替代狭隘的民族观,让社会对国内所有的穆斯林都更加包容。只有当土耳其人首先认为自己是穆斯林其次才是土耳其人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对同是逊尼穆斯林的叙利亚阿拉伯移民产生包容的情怀,迈出接纳他们的第一步。
所以综上所述,埃尔多安目前处在一个处理难民问题的极佳历史机遇。政变之后,权力集中化使他能推行原本在更民主的环境下受阻的新移民政策,通过给予难民合法的工作和居民权来稳定国内安全局势,并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时一样用数百万外来人口的技术与劳力来大力推动国内经济发展。
而融入的过程需要国家继续推行社会与文化的伊斯兰化来建立一个弱化了民族主义的、以宗教认知为基础的接纳阿拉伯移民的社会环境。这将推翻凯末尔建国时对土耳其社会的展望,并将会把埃尔多安与凯末尔派的世俗化精英针锋相对,加剧土耳其社会的阶层对立。这一切对这个传统温和派的穆斯林总统来说必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结语
与凯末尔面向欧洲的愿景不同,埃尔多安理想的土耳其是当年以传统出发展望世界的奥斯曼帝国,而奥斯曼君主们对民族和宗教多样性的宽容则是当下土耳其所缺失的。国际化的胸怀不仅仅是建国际机场、发展旅游和商贸等表象的东西,它需要国民有着对民族宗教的宽容和对自身与世界文化的理解。
说到这里,我想用一个我的自身经历来阐述一下土耳其的文化现状:今年夏天我在海峡大学的校园里与土耳其同学聊天时曾经讨论到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令我惊讶的是,我的绝大多数朋友们竟然都对他们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很多人甚至打趣地问我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在美国上学的中国人要学习这些连土耳其人自己都不想去了解的「旧历史」。他们认为这些历史是土耳其人耻辱而落后的过去,便不愿意去主动了解。
在我看来,只有去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更好的正视自己民族的得与失,只有去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才能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有更客观实际的理解,只有去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明白文明的本质,从而对与自己不同的民族和宗教更为接纳与宽容。
如果一个国民对自己的过去都一无所知,那么他们何谈去接纳他人融入世界呢?
文 \ 王达维
注:本文首发于头条号中东研究通讯,中东研究通讯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http://weixin.qq.com/r/r0N0bMLEVZ8qrYYP9xa9 (二维码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