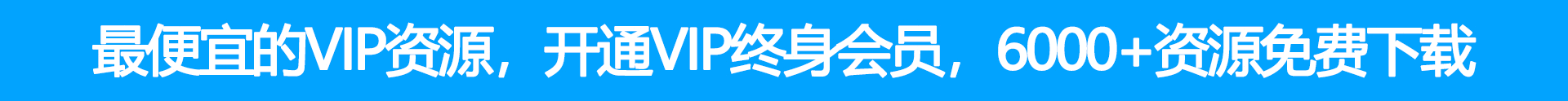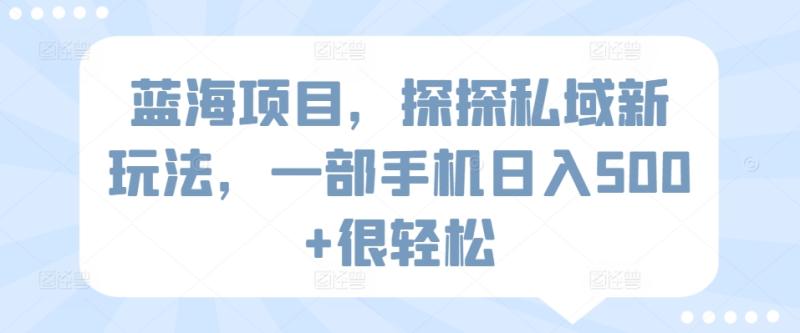八十年代筒子楼里的迷茫青年,他们有并不美好的残酷青春
紫阳十记(五)
爱民和建洲
在我的记忆中,爱民和建洲的形象既清晰又模糊。说清晰,是因为他们的特点实在太鲜明。他们的惊鸿一瞥,就足以令我终生难忘;说模糊,是因为30多年的时光利刃切碎了我的记忆。他们的形象虽时常闪现于脑海,但要想工笔画出,却难比登天。
这种似真亦幻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埃兹拉?庞德的《地铁车站》“在地铁车站/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因此,我写爱民和建洲,也只抽取他们的精神“意象”。正如,若从艺术的本质出发,蒙娜丽莎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那“神秘微笑”的意味;梵高所画的农鞋属于哪个农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双农鞋所隐喻的生活。
我在前文写到了亮和小朗,他们都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陕南小城紫阳所仰慕的青年。而爱民和建洲,我只是远远地看,并谨慎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
爱民上高二,他有个弟弟,和我一般大,常一起玩耍。我到他家玩时常碰到爱民。但爱民从不理我,只是干自己的事。他的冷漠反倒勾起了我的好奇,在和他弟弟玩的时候,我暗自打量爱民。
他个头中等,瘦。皮肤白净,脸有棱角。戴黑色眼镜,目光深邃,像有重重心事。他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清秀,书卷气十足。
但我没想到,爱民却是个狠角色。
据说有一次,因为在县体育场打篮球时遭遇对手故意肘击,爱民的眉骨被撞裂,顿时血染衣襟。队友群情激愤,冲上来围住肇事者理论。但作为受害者的爱民却表情平静,他态度坚决地喝退了队友,制止了这场可能发生的群殴。之后,他走到篮球场边的卫生间,把头埋进洗手池,用哗啦啦的凉水洗去血迹。但眉骨脆弱,一旦开了口就止不住血。血冲净了又流,流了又冲。无奈之下,爱民最后只能用毛巾捂住伤口,悄然离去。
一周之后,爱民悄然而来,他在一条背街里堵住了上次打破他眉骨的那个小子。他二话不说,抄起一块石板,重重地拍在了对方的脑袋上……
这一击造成了“脑破天惊”的严重后果。这个小伙头部重伤,差点丧命。幸亏抢救及时,才逃过一劫。但却落下了终身残疾:脑损伤导致语言障碍,被迫退学。
爱民闯下了大祸,差点被关进少管所。据说是因为他父母赔给对方一大笔钱,对方父母考虑到自己家经济困难,再三权衡之后主动撤诉。也因为对方父母口风有变,原本要被学校开除的爱民也保住了学籍。
这件事是爱民的弟弟给我说的。他自爆家丑时甚至还有点得意洋洋,意思是因为有了这个心狠手辣的哥,就没人敢欺负他。我当时年纪也小,听的时候也不免心生羡慕。
经此一战,爱民在县城声名鹊起。许多不上学的街头混混都主动拉拢他入伙。但据说爱民全都一一回绝,不屑与这些举止粗俗,整天偷鸡摸狗的混混为舞。
和传说中的凶狠甚至残忍全然不同的是,我看到的爱民从来都温和安静。他衣着整洁、干干净净。没有文身,不留光头也不留长发。文气十足的眼镜片之下,是他炯炯的眼神,绝无心浮气躁者目光中那种闪烁和游移。
传说中爱民和生活中的爱民到底是不是一个人?酿下大错的爱民就一定是坏人吗?我感到迷惑。也许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明白人是复杂的动物。好人也可能“贼眉鼠目”,坏人也未必不能文质彬彬。犯了错的好人未必就是坏人,干了好事的坏人也未必能成为好人。
爱民形象和印象之反差在建洲身上并不存在。从进入我的视线起,建洲就是一个行踪不定的“隐身人”。
其实这个“隐身人”是我正儿八经的邻居。我们两家紧挨着,他家在二层筒子楼的最里边。只要他回家,就会经过我家窗前。
建洲瘦,高。眼睛大,眼窝深。长发,有游吟诗人的忧郁气质。
他的家庭很特殊。他和姑姑同住,姑姑是个天主教徒。据说,建洲是过继给姑姑的,因此他有怎样的原生家庭,我一无所知。
建洲的生活轨迹毫无规律。他按时放学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因为我当时在家门口用纸箱搭了一个窝棚,放学后经常和小伙伴钻进去玩。这个违章建筑刚好处于交通要道,无论谁走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隔三差五,我才能看到建洲从我的“岗楼”前经过。他好像从未展现过笑颜,每次都木然地走过长长的楼道,甚至连碰到我爸妈也不打招呼。他轻轻地开门,又轻轻地关。然后,他家里就是长久的寂静。
这么安静的家庭在那个年代的筒子楼里相当罕见。因为锅碗瓢盆的撞击之声和普通人家的吵嚷之声才是筒子楼的主旋律。
现在想来,筒子楼真是毫无人性关怀的一种建筑,楼道里堆满蜂窝煤和烂家具,家家门口都有锅灶。室内都是直愣愣的开间,私密性极差,一股风吹起窗帘,就能一览无余。
我曾经偷窥过建洲家,因为好奇他家为何寂静无声。透过他家窗帘的缝隙,我看到了一个冷寂的家庭。没有电视,没有电扇,也没有收音机。没有沙发,没有茶几,也没有书架。只有床、椅、桌等不能再少的家具,建洲家别无长物。
唯一和别人家不同的人是,在里屋靠墙处的桌子上放置着一尊圣母像。在这个冷寂的空间里,她看起来肃穆却孤单。
此时我才似乎有点明白,为什么建洲不是天天回家。这个家过于朴素也过于冷寂,毫无家的温暖。这里只是他的宿舍,而不是安放身心的港湾。
建洲必然常常夜不归宿。据说他像个流浪汉一样夜宿于几个打工朋友的出租房里。
他的生活状态显然已经失常,一不小心就会滑入深渊,我想。因此每当县里开公捕大会时我都忍不住想问问爸妈,那里面有没有建洲。这种问题我爸妈自然也无法回答,于是我连续几天心情都惴惴不安,只到建洲再一次表情木然地经过我的窗前……
建洲不是坏人,他只是个缺少家的温暖的不幸青年,我想。从建洲身上,我看到了另一种青春。这种青春并不美好,它苦涩难言。
从此,我再也不会不加辨析地赞美青春,就如我再也不会义正辞严地鄙视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