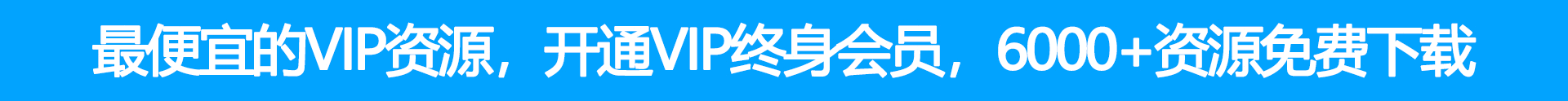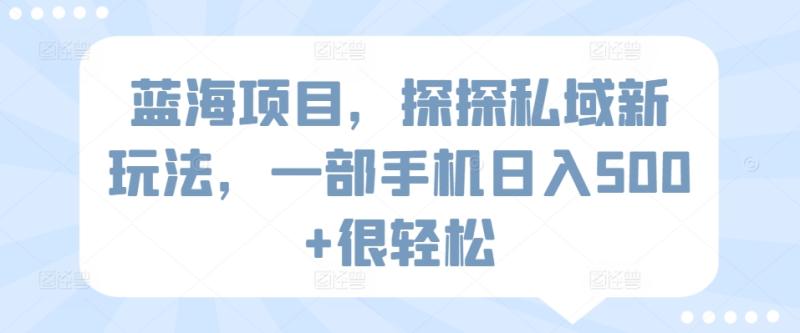译论||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重构:以卫三畏英译《聊斋志异》为例
本文来源:《中国比较文学》2018第3期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摘要:卫三畏是最早将《聊斋志异》中的部分故事译介到英语世界的西方汉学家之一。本文探讨其散见于《中国总论》《拾级大成》以及《中国丛报》中的选译故事对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重构, 并指出卫氏的翻译策略主要表现为文学文本的宗教化处理、直译形式下的意译改编, 以及选译策略下的主题重构。其翻译策略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一方面, 卫氏无视中西方读者对同一故事主题阐释视角的差异, 从词语的选择、叙事视角的转换, 以及情节的删减来引导读者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 他的传教士身份使得其译本被贯注了很强的宗教价值导向,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文的叙事重构, 以期证明在中国传教的可行性、必然性及迫切性。
关键词:卫三畏; 志怪小说; 叙事重构; 意译; 选译;
作者简介:张强, 文学博士,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比较诗学与文学翻译。
一、引言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的杰作。自19世纪以来, 随着美国来华传教士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 (Karl Gutzlaff, 1803-1851) 等人的译介, 逐渐为西方读者熟知。卫三畏受教会委派, 于1833年应募为印刷工来华, 协助美国传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eman) 等人编辑《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 , 该丛报以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纪实方式, 全方位记载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文化、风俗、医疗、艺术以及宗教生活等信息。
国内学者王燕在考察了《中国丛报》1842年第11卷第4期的一篇关于《聊斋志异》的介绍性文章之后, 认为该文的作者应为郭实腊, 早于卫三畏1848年《中国总论》中的两篇译文《种梨》和《骂鸭》。(1) 这一观点挑战了王丽娜认为“最早发表《聊斋志异》单篇译文的译者是卫三畏” (214) 的论断。然而, 顾钧认为“卫三畏与聊斋的关系并不局限于《中国总论》” (198) , 因而, 在谁是《聊斋》最早的译者的问题上, 学术界尚存在争论。
卫三畏关于《聊斋志异》若干故事的介绍与翻译, 散见于《中国丛报》《拾级大成》, 以及《中国总论》等著作中。他对故事的引介有一套自己的原则, 在上述著作中涉及《聊斋》故事选段的翻译, 也都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以阐释其看待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从一定程度上说, 卫三畏《聊斋》故事的英译是对中国志怪小说叙事模式的改编, 这一方面归因于他对原文本的删减与评论的改写, 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将译者的主观话语强加于文本之上, 过于宣扬文学的宗教教化目的,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误导读者的嫌疑。当然, 与他同时期的晚清文人对外文著作也存在“改述、重写、缩译、转译和重整文字风格等做法” (王德威103) ,相比之下, 卫三畏在翻译的形式上则很大程度地忠实于原文本, 他的意译策略在于对个别关乎主题阐释的关键词的意译、情节的选译与重组, 以及重写故事文末评论, 以期在情感与意识形态导向上偏离原著作者的意图。
二、以语言教学为目的的《聊斋》英译
以语言教学为目的的《聊斋》英译主要收录于《拾级大成》, 英文名称为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Dialect (《汉语简易教程:便于该语言学习的递进式练习, 尤适用于广东方言》) 。作为一部汉语教材, 该书于1842年由澳门香山书院出版。在前言中, 卫三畏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的编写目的:“为那些无论身在中国或海外的汉语初学者所著, 并希望那些身在国外, 或正在来华途中, 或已经抵达中国的海外人士从中获益” (Williams [13]2:1) 。(1) 顾名思义, 该书循序渐进, 由浅入深, 分为10个章节:部首、字根、读写方式、简单阅读、对话、阅读文选、量词、汉译英、英译汉, 以及阅读与翻译练习。其中有3个章节涉及到《聊斋》中的故事, 分别是第6章选译了《种梨》《曹操冢》与《骂鸭》3个故事, 第8章汉译英选用了《鸟语》《红毛毡》《妾击贼》《义犬》和《地震》5个故事, 第10章的阅读与翻译练习选用了《鸲鹆》《黑兽》《牛飞》《橘树》《义鼠》《象》《赵城虎》《鸿》与《牧竖》等9个故事, 而未给出自己的译文。
在第6章与第8章中, 为了便于读者学习中文, 卫三畏先是列出了汉语原文, 并在每个字的正下方列出了其广东话拼音, 接着在拼音下面列出逐字的英译, 之后在脚注中给出符合英文表达习惯的译本, 例如《种梨》第一句:
中文原文:有乡人货梨于市, 颇甘芳, 价腾贵。
广东话拼音: yau heung yan fo liüshi, p’o kom fong, ka t’angguai.
英文字对字逐译: a village man peddled plums in market, rathersweet fragrant, price rise high.
脚注英文译文:Once there as a villager selling plums in themarket, which were rather sweet and fragrant, and the price was high. (Williams1842:[13]
由此可见, 卫三畏在《拾级大成》中采用此种翻译编排的主要目的, 是方便汉语学习者阅读并理解选篇, 这就意味着字对字、句对句的直译是他所必然采用的翻译策略。这不仅符合汉语初学者的语言认知规律,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 也有助于研究卫三畏的措辞风格。然而, 此种以逐字翻译过渡到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译文的翻译策略, 容易使读者误认为卫三畏仅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实际上, 在涉及故事主题的词句时, 卫三畏主要采取意译的策略, 以向读者传达他所理解的故事主题。这在《拾级大成》中的《聊斋》故事的翻译上已经有所体现, 主要表现在故事题目的翻译上与关乎主题表达字句的词语选择两个方面。
故事题目翻译方面, 卫三畏基本没有沿用《聊斋志异》中故事的原标题, 而将其重新命名, 这些命名都直指故事主旨或重要线索, 类似于《伊索寓言》中故事的命名方式, 这可从分析第6章与第8章中选译的故事标题中看出:
由上表可见, 在卫三畏翻译的8个故事标题中, 除《曹操冢》 (1842:120) 采用直译 (Grave of Ts’oTs’o) 外, 其余故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从情节陈述到故事主题表现上的意译, 甚至改写。这一方面服务于《拾级大成》的编写宗旨, 有助于汉语学习者理解故事选段的内容、情节与主题;另一方面, 也暗示卫三畏作为中国文学的传播者, 对该书的读者有着强烈的价值导向与期待。在《拾级大成》一书的前言中, 卫三畏就已指出汉语学习的目的, 即“促进高尚的基督教义在中国的传播” (1842:iv) 。
《拾级大成》中故事翻译在排版形式上基本忠实于原文, 但这并不意味着卫三畏对故事主题所映射出的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价值取向的认同。在上述8个故事的译文中, 其中有4篇故事 (《种梨》《骂鸭》《曹操墓》《妾击贼》) 的末尾有异史氏的评语, 一般直接讲明故事主旨。异史氏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自称, 意为作者记载的故事怪异荒诞, 并非正史。然而, 卫三畏却有意规避异史氏的评论, 在《拾级大成》的选文中删除了蒲松龄对这些故事的评论。卫三畏没有在这本汉语教科书中对这些故事做主题上的阐述, 然而, 在他后来出版的《中国总论》等著作中, 集中体现了他作为译者与文化传播者对这些故事的主观阐释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三、以传播价值观为目的的《聊斋》英译
《聊斋》的英译在《拾级大成》中被用作汉语学习的阅读材料, 在其后来出版的《中国总论》中也被用来阐释卫三畏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国总论》最早出版于1848年, 是卫三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风俗、宗教以及社会背景等诸多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在美国汉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第11章“中国经典文献”与第12章“中国的雅文学”集中探讨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尤其在第14章, 他指出中国文学在维护社会制度与巩固统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欧洲人从道德或物理科学范围[了解中国]可能所获不多, 而更应该从他们纯文学的取之不尽的宝藏中去探索” (2005:469) 。《聊斋志异》以其主题的多样性、人文地理景观描述的丰富性、题材选择的广泛性, 广为西方学者翻译与介绍。卫三畏曾说:“《聊斋》因其内容多样、表达力量强而受到青睐, 可以推荐给每个想研究中文的丰富词汇的人加以细读” (2005:482) 。卫三畏意识到了《聊斋志异》在中国是通俗读物, 但他仍将其归入雅文学的范畴, 一方面因其寓言故事的体例、丰富的词汇与庞大的读者群;另一方面, 他以欧洲文化范式下对纯文学 (belle-lettres) 类型的划分, 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小说与诗歌、戏剧等体裁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 “我们毫不迟疑地承认他们以戏剧、诗和小说组成的纯文学领域, 在我们的眼光中总是具有最高的地位” (2005:469) , 殊不知明清小说在当时并未进入士大夫阶层所谓雅文化的讨论范畴。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中第三部分“子类”下属的14个分类, 卫三畏分别简要阐述了每一类著作的主要特点。他主要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例介绍第12类———小说, “包括寓言、故事, 在中文的数千种这类作品中所列寥寥无几[……]这些书成了较低阶级的普通精神食粮, 能读的就读, 不会读的也一起谈论;其影响自然相当大。有许多是用最纯的风格来写” (2005:481) 。在《聊斋》故事的文本阐释方面, 卫三畏与蒲松龄的观点可谓大相径庭:前者以故事为例说明以基督教义改造中国社会的必要性, 后者以具体故事为素材描绘市井生活, 其主题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卫三畏对《聊斋》故事的翻译进行了叙事的重构, 这种重构可以通过他同时期对中国宗教与小说书写范式的视角关注中得以印证。
《种梨》最早被选译刊登在《拾级大成》, 后来被收录到《中国总论》中, 并稍加修改, 借以阐释卫三畏关于中国雅文化中小说的地位与特点。《种梨》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道士向卖梨人讨要梨子, 卖梨人呵斥其走开。旁边店里的伙计见两人争吵, 就向卖梨人买了一个梨赠予道士。道士施魔法, 将梨核种入土中, 迅速长出参天梨树, 结满果实, 并将其分予众人。卖梨人也混入人群看热闹, 竟把卖梨的事情忘了, 等回到自己的摊位, 才发现连梨带车都不见了, 才恍然大悟, 原来道士施法的梨木和果实都是取材于卖梨人的车把和待售的梨子。故事在众人对卖梨人的嘲笑声中结束。在故事结尾,
异史氏曰:乡人溃溃, 憨状可掬, 其见笑于市人, 有以哉!每见乡中称素封者, 良朋乞米则怫然, 且计曰:“是数日之资也。”或劝济一危难, 饭一茕独, 则又忿然计曰:“此十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 较尽锱铢。及至淫博迷心, 则倾囊不吝;刀锯临颈, 则赎命不遑。诸如此类, 正不胜道, 蠢尔乡人, 又何足怪! (蒲松龄2016:69-70)
显然蒲松龄站在了道士这边, 批评卖梨人吝啬、胡涂与愚蠢, 受到道士的愚弄与众人的嘲笑是罪有应得。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背景下, 蒲松龄教导读者不可为富不仁, 要兼济他人, 自己才可得福。然而, 卫三畏显然不赞同蒲松龄对这个故事的看法。在《中国总论》对这个故事的评价中, 卫三畏说:“中国人认为道教信徒是主要的魔术家, 这部书中有很多故事加以描写, 其目的也许在于抬高他们的技巧, 增添他们的声誉” (2005:482) 。卫三畏的评论集中于对作品的宗教价值解读, 这与蒲松龄所侧重的道德关怀相去甚远, 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卫三畏在《拾级大成》与《中国总论》中刻意漏译异史氏评论的原因之一。蒲松龄在《种梨》中将道士以正面人物的形象来塑造, 在卫三畏看来“可能因败坏道德遭到反对, 或是因情节离奇荒谬可笑” (2005:482) 。卫三畏更多地关注道士的身份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社会对本土宗教的盲从。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 (Joseph Edkins) 认为, “儒教讲求伦理特质, 道教具有物质性, 佛教则是形而上的” (59) 。道教的物质性在卫三畏看来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落后与迂腐。与儒教相比, “和尚、道士给予人们的只是迷信的恐惧, 他们说的道理是靠不住的, 所以不能俘获所有的人” (卫三畏2005:726) 。卫三畏认为, 道教并没有通过大量的论据来规约人们的社会责任, 因而“充满着无用的沉思或庄重的废话” (2005:726) 。因而, 可以推断, 卫三畏认为《聊斋》若干故事中 (例如《种梨》) 的道德败坏正在于对以道士为代表的道教权威的过分迷信, 从而导致了中国社会道德观的偏差。道士借助魔法实施了变相的抢劫行为, 违反自由买卖的市场原则, 致使卖梨人蒙受经济损失以及大众的道德绑架。《种梨》中的围观者作为中国社会群众的缩影, 正是卫三畏所要批判的对象。究其原因, 他将矛头直指道教与佛教的弊端。在《中国总论》的第三章“西部各省地理”中, 他曾这样描述广州道教圣地城隍庙:
广州城隍庙的主管人为了谋到这个职位付出4000美元, 他可以卖香烛给朝拜者, 几年内就捞回这笔钱。广州庙宇都是阴暗沉闷的处所, 和住在里面的没活气的偶像以及无意义的仪式倒很相称。庙前场地通常是小贩、乞丐、闲人的地盘, 偶尔为了敬神, 搭起席棚来演戏, 才把他们赶走。偶像坐着的神龛设在主要厅堂中, 只在前面有照明, 祭坛、钟鼓以及庙中其他设施, 很少考虑到如何使之有生气;在小房间和内室居住的人, 几乎同他们所供奉的偶像一样无知觉, 这些可怜的人们过着寄生虫般的无意义的生活, 往往不过是邪恶、懒散和犯罪的外衣罢了。(2005:116)
在卫三畏看来, 道教不过是中国人谋求生计所利用的工具罢了, 具有极强的物质性与功利性。社会特权阶层借其卖官鬻爵, 使庙宇沦为敛财的工具, 社会底层人民渴求借以从统治者那里得到物质的怜悯。道教本身又没有系统地规约人的社会责任, 它宣扬出世的人生态度, 成为滋生腐败与社会丑恶现象的温床。卫三畏的这一论断虽有失偏颇, 但一方面映射出了中国社会的世俗政治力量远大于宗教力量的事实, 另一方面, 也为其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迫切性提供了事实依据。他认为, “所有人类征服者都有个缺陷———统治者对于赐予权力的上帝缺少应有的责任感” (2005:718) 。
四、《聊斋》英译的叙事重构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道:《聊斋志异》“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 然描写委曲, 叙次井然, 用传奇法, 而以志怪, 变幻之状, 如在目前” (164) 。他从故事情节、叙事策略、表现手法、创作主题, 以及艺术效果等方面, 充分肯定了《聊斋志异》在中国古典志怪小说中的地位。在鲁迅看来, 志怪小说不能狭隘地理解为记述“神仙狐鬼精魅”的故事, 还应包括“畸人异行”和“偶述琐闻” (164) 。换句话说, 志怪小说的主人公可为神仙鬼怪, 也可为世间凡人, 书写题材既可为神话传说, 也可为日常琐事, 究其核心, 就是故事情节的奇特性与怪诞性。
卫三畏在《拾级大成》中解释了选择《聊斋》中的故事作为阅读材料的原因, 即“完美的文体与纯粹的汉语” (1842:157) , 后来又进一步在《中国总论》中总结了《聊斋》的特点:“内容多样”、“表达力量强”、“中文的丰富词汇”、“情节离奇荒谬” (2005:482) 。尽管卫三畏没有用“志怪”一类的字眼来概括《聊斋》的体裁, 然而他与鲁迅所概括的志怪小说的诸多特征不谋而合。事实上, 卫三畏所译多数故事都属于“畸人异行”与“偶述琐闻”的范畴。
卫三畏的《聊斋》英译作为跨文化的翻译实践, 其目的并不局限于字对字、句对句的文字及语句的转换 (尽管在《拾级大成》中他是这样做的) , 其要义在于以英译为载体, 重构与想象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空间, 这一空间可容纳异域读者、译者与评论者的视角, 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多元性的特征。作为翻译的叙事, “通过故事得以展现, 为我们带来‘远方的消息’。更展现这样的消息背后的‘与我同类’的某个/种生命现世存在的样态、风采和价值” (薛凌22) 。接下来,笔者将从词语的选择、叙事视角的转换, 以及情节的删减来具体分析卫三畏《聊斋》英译构建与想象出的这一叙事空间及其现实意义。
在词语的选择方面, 卫三畏的《聊斋》英译很大程度上是以汉语教学为重要目的, 这客观上决定了他忠于原文的翻译策略, 然而, 对某些词语的过度阐释甚至曲解, 则直指故事主题, 注入了译者强烈的主观话语及价值取向。
以《骂鸭》为例, 《中国总论》中的译本在《拾级大成》译本的基础上稍加修改。故事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 讲述了一位村民偷食邻居家的鸭子, 身患怪疾, 长满鸭毛, 被医生告之要被鸭子的主人大骂, 方可痊愈。村民在邻居老翁的刻意咒骂下, 最终痊愈。故事中叙述者的语气较为平和, 并没有体现明显的个人好恶与立场, 对故事情节作了较为客观的陈述。然而, 在卫三畏的两个译本中, 他对于个别词语的选择都贯注了叙述者强烈的情感色彩与价值偏好。
在故事的开始, 作者就介绍了主人公, “邑西白家庄居民某” (蒲松龄2016:1344) , 他无名无姓, 以“某”代之。在《拾级大成》中, 卫三畏将“某”译为“a certain commoner” (“某位平民”) , 较为准确地为汉语学习者解释了作为代词的“某”。而在《中国总论》中, 他将“某”译为“rustic” (“农夫”或“乡下人”) , 不仅直接表明主人公身份, 更暗含个性粗鄙之意, 直接表明了叙述者的情感偏向与立场。卫三畏的道德关怀体现在接下来对“翁”与“病”的翻译。故事中讲到邻家的老伯为人和蔼, 不轻易骂人, “邻家翁雅量, 生平失物, 未尝征于声色” (蒲松龄2016:121) 。在两个译文中, 卫三畏都将其意译为“gentleman” (绅士) , 不仅表明了对邻家翁德行的赞扬, 也概括了他对中国语境下“君子”风度的理解, 即”温和、勤劳且有耐心” (卫三畏2005:581) , 尽管他充分认识到中国人性格特点的多样性, 认为总结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是“比列举稀奇古怪事情困难得多的任务” (2005:580) 。此外,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故事结尾, “某益窘, 因实告邻翁, 翁乃骂, 其病良已” (蒲松龄2016:1344) , 卫三畏将“病”译为“disorder” (混乱) 。在极为忠实原文的《拾级大成》的逐字对译中, 他虽将原文中的“病”译为“disease”, 但在脚注中, 仍将“其病良已” (122) 译为“His disorder was removed” (122) 。显然, 在这里卫三畏采取了意译的策略, 并加入了自己对此语境下“病”的理解, 并非身体机能的异常与失调, 而是乡人偷窃邻家翁财产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与道德的挑战, 即蒲松龄所说的“天罚” (2016:1344) , 被卫三畏译为“a judgement from heaven” (上帝的审判) 。这颇具宗教意味, 暗示“摩西十诫”中“不可偷盗”的戒律。然而, 卫三畏将异史氏的评语略去, 并将题目改为《捉贼记》 (Williams 1842:[13], 并指出此故事旨在“从侧面规劝盗贼” (2005:482) , 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原作思想的复杂性。蒲松龄从偷鸭人与邻家叟的关系角度, 阐释了过错与美德、天罚与人罚等二元对立与辩证关系, 以“‘攘者可惧’‘骂者宜戒’‘以骂行善’层层推进, 为习见翻案, 最后意在说明常人皆以骂者心不慈, 其实骂人是在行善, 当为真仁慈” (张雅媚235) 。异史氏的以骂行善论暗含道家以阴阳为隐喻的二元对立的动态转化观念, 这与卫三畏所主张的上帝审判的绝对权威性, 以及“摩西十诫”对偷盗行为零容忍的教义是格格不入的。这也强有力地解释了为何卫三畏删去异史氏对故事主题的评论。
要对译文叙述视角的转换进行分析, 我们首先应了解中西小说叙事视角范式的异同。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援引法国汉学家雷穆萨对中西小说叙事风格的评论:
他[雷穆萨]简要地指出中国小说的主要缺点在于对琐碎细节、地方外观以及对话者的性格背景作冗长的描写, 而叙事的主线大多以谈话的形式来体现, 写得太细致, 很快使人厌烦[……]在有趣的情节中间以最严肃的态度谈起道德思考, 就像喜剧中的长韵律赞美诗, 搞混了主要故事, 把理应产生效果的统一性打乱了。(卫三畏2005:483)
雷穆萨意识到了中国小说的复杂性, 一方面在于对细节的处理与背景信息的细致描写, 多用外部视角来展现故事人物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 又注意到小说的说教性所导致的对故事结构与语言风格的破坏。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小说叙事话语与视角的复调性。中国传统小说中经常可见批注与文本并行, 叙述者也可随时以他偏爱的形式, 以严肃、幽默、调侃, 或是感慨的语气评论故事情节本身或故事人物性格特征, “作者、叙述者, 评论者以及读者在同一小说中有可能集体登场” (Gu 313) 。这决定了小说叙述视角转换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聊斋》中的众多故事都不局限于一个叙事视角, 而是掺杂着故事叙述者、作者、故事人物等众多视角, 具有开放性, 并主动邀请读者对故事主题与寓意进行探讨, 因而, 其说教的形式并不单调, 这也解释了卫三畏认为蒲松龄“几乎不存在虚伪的说教” (2005:482) 的原因。
以《地震》为例, 故事以小人物为对象, 记载了康熙七年 (1668年) 发生的郯城地震, 因极震区在山东郯城而命名。这场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可能由于蒲松龄所在的临淄距离震中较远, 生命财产损失并无如此惨重, 因而, 故事叙述者的笔调较为轻松, 甚至带有幽默与喜剧的色彩。故事分为两段, 第一段的叙述者“我”是个亲历地震的小人物, 以全景的视角描述了周围的建筑、河水的倾泻、牲畜的慌乱, 以及街上因慌张逃窜而顾不得穿衣服的男女。第二段转为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故事情节与地震并无大关系, 讲述一名妇女深夜如厕, 回来的路上发现孩子被狼叼走, 因而顾不得穿衣服而去追回孩子。然而, 异史氏在结尾巧妙地将两个故事的主题联系起来, 并说这位夫人的举动与地震中顾不得穿衣服的男男女女如出一辙, 指出“人之惶急无谋, 一何可笑” (2016:343) 。显然, 蒲松龄欲表述的故事主题是人在慌乱中往往会忘了本应关注的重要事情, 这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尤为重要。卫三畏的译文有意删去了妇人救子的片段以及叙述者的主观评论, 只保留第一段关于地震场景的第三人称全景视角描写, 将“非常之奇变”译为“extraordinary phenomenon” (非凡的现象) 。原文中强调地震带来的地理景观的变化, 而译文则侧重作为地震本身的现象呈现。卫三畏摘译的这段第三人称全知全景视角下的地震景象, 与《圣经·以赛亚书》中对地震的全景式描写形成了强烈的呼应, 其目的在于指出末日降临之时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共同场景, “地上的居民哪, 恐惧, 陷坑, 网罗, 都临近你” (《以赛亚书》24:17) , 而此时, 人类将面临共同的命运:
看哪, 这些从远方来, 这些从北方, 从西方来, 这些从秦国 (Sinim) 来。诸天哪, 应当欢呼, 大地阿, 应当快乐, 众山哪, 应当发声歌唱, 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 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以赛亚书》49:12)
关于《圣经》中“Sinim”是否指中国, 学界尚有争论。然而, 或许出于在中国传教的客观现实需要, 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们普遍认为“Sinim”一词指代中国。受“千禧论”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卫三畏, 在翻译《地震》故事之时, 自然融入了他对中西两个世界在末日地震之中所面临的共同命运的见解, “乃支配卫三畏重写《聊斋》以至中国文学时的意识形态” (张雅媚237) 。可见, 秉承着以基督教启蒙中国的理念, 卫三畏始终认为“上帝还未以他的仁慈施予中国, 他以自己的方式等待着中国去学习他的律条” (Williams 1889:[15]。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卫三畏选取宏观的全知视角, 而刻意避开与这一理念无关的细节描写与人物形象刻画, 以宏大叙事展示出上帝的权威性, 暗示中西两个世界终将得到由上帝审判的共同命运, 为其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社会的理念提供了文本支持。
叙述者在故事叙述中的角色对于故事主题的阐释与叙述视角的转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多数批评家认为, 我们不应将叙述者与作者混淆, “除非作者提供真实的背景或公开发布声明, 将自己与叙述者联系在一起” (Beardsley 213) 。赵毅衡也认为, “叙述者既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 他就拥有自己的主体性, 就不能等同于作者, 他的话就不能自然而然当作作者的话” (26) 。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与叙述主体的叙述者在《聊斋》中基本上是一致的。大多数故事采取第三人称全知或有限视角来讲述故事, 而故事结尾处的异史氏以野史史官的身份和语气来评说故事主题, 这是古典志怪小说的一贯模式。王平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中认为, 史官式叙述“作者与叙述者相同一, 因而对于所要叙述的人或事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11) 。因而, 叙事者无需任何中介即可完成视角的任意切换, 全方位地将故事讲述给读者, 很少有不可靠叙事者的存在。其最终目的是以史官评述的方式来揭示故事主旨, 以达说教之目的。而这种说教性的结尾评论, 被卫三畏有意删减, 甚至加之以自己的评论, 达到他所期待的宗教隐喻。
情节的删减也体现出卫三畏在英译过程中的道德关注。《商三官》是唯一一篇收录在《中国丛报》中的译文, 也是卫三畏借以阐释复仇主题在中国文化中呈现方式的重要作品。该文讲述少女商三官的生父被豪绅所杀, 然而官府却不能主持公道, 因而商三官女扮男装, 为父报仇。在译文中, 卫三畏做了两处重要的删减, 其一是豪绅家的两名仆人对商三官奸尸而丧命, 其二是结尾异史氏的评论。取而代之的是译者重写的评论:
这类行为[商三官的复仇行为]为中国的道德家所赞颂, 尤其是在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与不公正审判的情况之下, 而导致罪犯的行为没有受到相应惩罚。无论此事是真是假, 这则故事说明了中国人认为父母之仇是一定要报的。这也与希伯来人以血还血的观点进行比较提供了话题基础。(Williams 1849:401)
可见, 卫三畏对故事情节的删减直接服务于对故事主题的阐释。通过商三官复仇这一故事, 卫三畏试图寻求中西文化对复仇主题的认同, 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文化与《圣经》的主题联系, 这一方面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话语上的亲和力;另一方面, 也为基督教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建立了共同的话题基础。其实, 蒲松龄并非想凸显复仇的故事主题, 在故事末尾, 他说, “愿天下闺中人, 买丝绣之, 其功德当不减于奉状缪也” (2016:732) 。蒲松龄认为商三官的复仇壮举令男子都望尘莫及, 他关注的是封建社会中女德社会典范的树立。而卫三畏的译文及评论则抹杀了性别角色在故事中的重要作用, 这包括仆人的奸尸行为, 在卫三畏看来有伤风化, 且与复仇故事主题无关, 因而不难理解其删去这一情节的主观意图。
五、结论:翻译与叙事重构
志怪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中向来不仅仅停留在神怪奇谈的层面上, 而往往被赋予教化大众的社会责任。《聊斋志异》正是利用了佛、儒、道于世有补的积极作用, 教化人们弃恶从善、因果有报、邻里互助等道德观念。它作为通俗小说的教化兼娱乐目的, 在中国语境下远大于其宗教意义。所谓人鬼之界, 也并非宗教意义上的世界划分, 而是以道德作为准绳的区分, 用蒲松龄自己的话来说, “德则其人也, 不德则其鬼也” (1986:67) 。神鬼形象的呈现并非志怪小说的核心要素, “超自然、神奇与魔法不仅组成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元素, 而且已成为情节与显性的结构设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Gu 331) 。志怪小说在于其离奇故事的隐喻性, 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折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也体现在蒲松龄以短小故事以及文末评论的方式引领读者的价值判断。
卫三畏显然注意到了《聊斋》故事极强的价值导向性, 也注意到故事中所呈现出的中国社会对儒、道、佛的宗教思想的侧重, 及其与基督教在道德关注上的异同。作为早期来华传教士, 他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社会的理念对其翻译实践有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在《拾级大成》等以汉语教学为目的的教材中, 卫三畏以字对字、句对句的方式翻译《聊斋》中的若干故事, 形式上忠实于原文, 但实际上其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的叙事实践,这表现在他对词语的选择、叙事视角的转换, 以及情节的删减等方面:一方面有意规避蒲松龄对原文故事的阐释, 另一方面选取宗教隐喻强烈的词语, 甚至重写文末评论的方式暗示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社会的可行性、必然性, 以及迫切性。卫三畏以其常年居于中国的经验、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熟知, 以及对忠实翻译的标榜, 实现了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重构。寻求中西两个世界的宗教道德认同, 是他以宗教改造中国的宏伟蓝图中的重要一环。1879年,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卫三畏在中国任职的辞呈, 并总结了其外交与文化贡献:“更为重要的是, 宗教界不会忘记, 尤其多亏了您, 我们与中国订立的条约中, 才得以加入自由传教这一条” (卫斐列2004:281) 。以《聊斋志异》的英译为例, 实现其传教宏图的主要手段则表现为文学文本的宗教化处理、直译形式下的意译改编, 以及选译策略下的叙事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