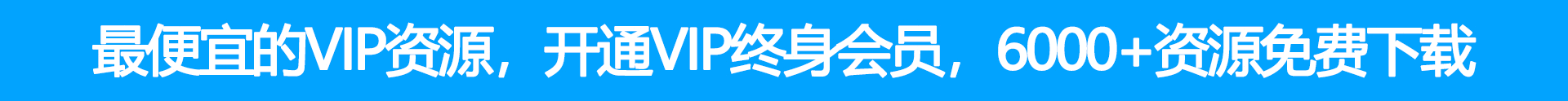“午夜摆渡人”代驾司机的别样人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人们往往把目光和话题聚集在公众人物身上,很少有人关注那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群体,比如代驾司机。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他们毫不起眼地被淹没其中,但在公众视野之外,他们同样有着一个丰富的世界。
他们聚集在灯火辉煌的酒店、KTV周边,在他人的觥筹交错间静候一单生意。他们在把握方向盘的同时,也在弥漫的酒味儿中围观他人或悲或喜、或亢奋或颓然的形形色色的人生片段。
多数代驾司机
都是第二职业
1月11日夜间,邵志超把妻子和8个月大的女儿送到了父母家,直到8点多才走上街头,打开软件,在寒风劲吹的街头边溜达边等待订单出现。若在平时,他完全可以到某个酒店的大堂里坐着,跟同行们聊天,顺便向一些酒局散场的人发名片。而这个夜晚,他没打算多干,“媳妇发烧了,晚上还得回家给孩子洗澡。”
和其他代驾司机一样,“趴活”的时候邵志超时刻把手机握在手中,生怕听不见订单响起的声音,订单一来就得马上给顾客打电话。
除了正常穿着,邵志超的工作服就是一个马甲,马甲胸前的LED胸牌闪烁出他的所属公司——紫星代驾。
“这个工作比较自由,老板说了‘想挣钱就出来干活,不想挣钱在家歇着也没人管’。”邵志超说,“钱是给自己挣的,只要不懒就有钱挣。”
这个时候,邵志超的老板也没闲着,尽管软件可以智能地直接往路面上分配订单,他还是为了“踏实一些”选择值班。紫星代驾的老板叫戚维峰,“2013年就开始干代驾公司,中间‘死’过一次,去年又重新开办起来了。”
2013年,威海有七八家代驾公司,2016年增至十五六家,至今又降至七八家。“代驾市场还不大规范,本小利薄,不是很好干。”戚维峰说,“别的公司是从司机身上抽取10%到20%的提成,我这里是每月收400块钱的管理费。”紫星代驾有50名代驾司机,但这并不代表戚维峰每月能挣到2万元,“搞培训、买商业险,都是不小的成本。”
“收管理费而不收提成,就是让司机觉得每笔钱是给自己挣的。”戚维峰说这是自己的独到之处,“全职司机一个月能挣1万多,只干夜班的也能挣四千左右。”
目前,威海街头约有800名代驾司机,绝大多数是“夜班兼职”。戚维峰并不认可“兼职”这个说法,“叫‘第二职业’更合适。公司跟他们签订了合同,这就是一份工作,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那种散兵。”
每晚接三四单
月挣三四千元
戚维峰说,代驾司机都是“缺钱花才来干这个的”。
32岁的邵志超在一家公司上班,“每月两千五六百块钱,不够开销”。去年5月份,女儿出生后,妻子辞职干起了全职妈妈,家庭收入骤减,花销却飙升,邵志超不得不把业余时间从“看孩子”挪用到“第二职业”上,“每天晚上干几小时,一个月就能挣三四千。”
每晚平均能接到三四个订单,挣钱多少则取决于运气,“好的话能挣好几百,差的话就只有几十块钱。”这种运气跟订单的远近有直接关系,订单若是集中在市区短短几公里范围内,他就可以不断接单、送客、再接单,收入不会少;而如果订单较远,不能推却的订单就往往要耗去半夜,“前几天,从市区送一个顾客去温泉镇,都走到山里去了,这单挣了70多块钱,一晚上也就干了这一单。”为了这一单,他从山里步行5公里走到了江家寨,打电话喊来父亲,父亲骑摩托车把他接回了家。
有时,长距离订单也是非常划算的,邵志超曾接过去往荣成石岛的单,“80多公里,一单200多块钱,再花几十块钱搭顺风车回来。”去年夏天,他也送过去往文登区、乳山市的顾客,“文登那一单是大半夜骑电动车回来的,乳山那一单实在太远,找个旅馆睡了半宿,大清早坐客车赶回来上班。”
收工后如何返程是代驾司机们最为头疼的事,拼车、打车、骑共享单车,乃至步行都是选项,最好的选项是就地再接一个能回到离家不远的订单,但这种订单出现的几率很少。他们的选择往往是把折叠电动车搁到顾客的后备厢里,骑行回来,但这个选项只是夏夜的明智之选。邵志超开着自己的车出门,但返程往往是靠父亲,“一般都是我爸骑摩托车去接我,否则挣的钱又花在打车上了。”
在寒风里哆嗦十几分钟后,一个订单如愿而至。邵志超赶紧打电话过去,“哥,我5分钟内到,您看行不行?”顾客在古寨西路,邵志超不得不赶紧驱车赶过去,“5分钟内必须赶到,这是公司的规定。”
代驾司机都有着被分配好的活动范围,邵志超的范围是文化路的珍珠利华酒店到体育场一带,这段长约3公里路段周边的百余家大小饭店、夜总会都是他的“地盘”。接第一单时,邵志超往往是开着自己的车去接,之后接单还是要看运气,运气好的话能就地继续接单,运气不好就要想办法再回到自己的“地盘”上等候下一单的出现。
行业门槛不高
只能尽力规范
21时前,5公里以内收费是28元,21时至次日1时是38元,1时后则涨为48元。除了起步价,每超过1公里加5.5元。“这个价不算便宜。”戚维峰说,“所以,找代驾的人一般是有守法意识,有素质,收入较高的人,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跟顾客发生纠纷。”
虽然干代驾的时间只有8个月,邵志超已经开遍了各种车型,听过各种方言乃至外语,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滋味儿并不好受。在酒精的刺激下,很多人一改平日的样子。有人为了从80元的代驾费中砍价20元而大为光火,邵志超则在顾客的咒骂声中沉默着离开,“白干就白干,跟醉汉纠缠是件很无聊的事。”有人醉倒在车内昏迷不醒,邵志超在他的车内坐了足足半宿直到他醒来,“必须确保顾客安全。”有的顾客上车后一言不发,邵志超便在征求路线后默然驾车前行;有的顾客则亢奋地东扯西扯,邵志超只能出于礼貌回答几句;有的顾客会递根烟过来,烟瘾很大的邵志超却不能接,“妨碍安全驾驶的事一概不能做,包括聊天。”
成为代驾司机的门槛很低,有驾照、车技熟就差不多了,面试就跟相面差不多,“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很和善,是否容易跟人沟通,单纯地从一些表面现象来决定是否录用。”作为老板,戚维峰不是不想深入地了解应聘者的底细,但这些个人信息显然是他无法掌握的,他甚至希望公安部门能帮着代驾公司把把关,“想看看这人有没有犯罪记录,是不是经常交通违法,但这些也只有警察能做到。”
为了尽可能地规范,戚维峰在公司的培训上下足了功夫,从礼貌用语到规范操作事无巨细,以致有些司机觉得这是在“伺候财主”。“比如说要诚信,说几分钟内到就几分钟内到;还比如说要周到,打开车门,把手搭在车门上,防止顾客碰头;开车后,要问速度是不是合适、顾客舒服不舒服。如果被顾客投诉了,这个司机就要被扣分,被相应地从平台扣除一些费用。”
“大家都是想靠多出点力挣点辛苦钱。”戚维峰说,代驾司机中甚至也会有女人,“很少,估计现在全威海也就几个女的。”几年前,紫星代驾也有过一名唯一的女代驾司机,“她一出车我们就担心”,果不其然,这名女司机在被一名醉酒顾客强行抱了一次后辞职了,“女人干这行更不容易,总有些人不怀好意……”
有人欣然而至
有人愤愤离开
在代驾行业,人来人往永远是正在进行时,不时会有新人欣然而至,同样也会有旧人愤愤离开,这种“第二职业”注定只是多数人的兼职选项。“有人在各个平台间跳槽,也有人干一天就不干了。”戚维峰想尽办法来稳定队伍,“把人品好的老司机留住就是留住了骨干力量。”为了留住人,逢年过节发福利是必须有的,司机过生日也要送个大蛋糕。
冬天,订单集中在20点到21点之间。
时间已过21点半,邵志超迟迟没有等到第二单,他决意不再等下去,妻子和女儿还在等着他。说起女儿,邵志超不由自主地泛出微笑,“感觉一切都是为了她活着。”
坐公交车再步行几百米,他顺利取回了自己的车,赶到父母家再载上妻儿回家。下车时,女儿已经睡着,趴伏在邵志超的肩头,邵志超小心翼翼地把毛巾被给女儿捂得更严实一些,仿佛肩上扛着整个世界。
与此同时,还有众多的代驾司机正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每多接一单就多挣几十元钱,可以用来换取父母的药片和孩子的新衣服。
几个小时后,太阳还照常升起,他们又将出现在“第一职业”的岗位上谋生。
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陶相银
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