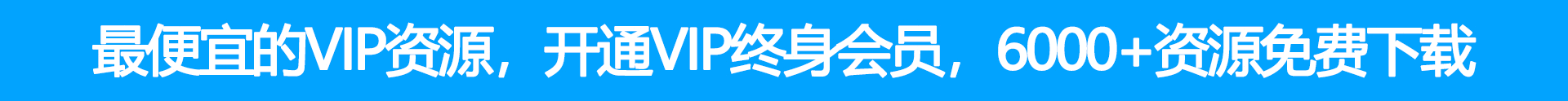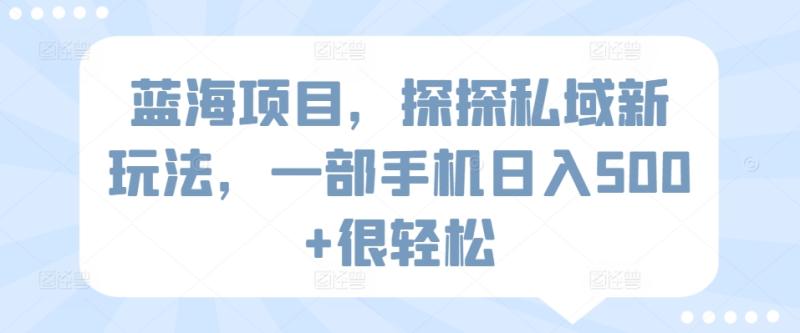汉语词汇系统发展中的语素类化
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即一组意义相近的同义或同类单音词,常由具有某一共同语素的词语替代。我们将之称为语素类化,即同义或同类词在语音表达形式上具有类聚性。语素类化可以分为同类词的语素类化与同义词的语素类化,后者常伴随着语义场内处于中心地位词的词义泛化。语素类化的本质是将同义或同类聚合中的共同性要素提取并以外化的词形体现出来,使同义或同类的聚合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类推性和有序性,是词汇从派生阶段到合成阶段词汇系统向有序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者简介:
卜师霞,凌丽君,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在汉语词汇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即一组意义相近的同义或同类单音词,常由具有某一共同语素的词语替代。如“寝”、“寐”、“觉”,意义相近,分布互补,差别在于动作状态的不同,但在发展中这些词所表达的意义均由“睡”利用自身或自身的组合“睡觉”、“睡着”、“睡醒”来代替,在语音上具有类聚性。我们将之称为语素类化,即同义或同类词在语音表达形式上具有类聚性。
从个体上来看,这些词在古今汉语的发展中均由一个短语来表达了的个体变化。很多学者对此均有关注。
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已指出:“白话里有许多动词常带一定的止词,合起来才抵得文言的一个动词。”①蒋绍愚提出汉语词汇从古到今有从“综合”到“分析”的趋势,认为“所谓从‘综合’到‘分析’,指的是同一语义,在上古汉语中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达的,后来变成或是用两个词构成词组,或是分成两个词来表达”②。石毓智把类似的现象归因为古今汉语动词概念化方式不同所产生的变化,认为“古汉语的动词概念之内包含有结果、地点、方向等方面的信息,现代汉语则是把这些信息与动作行为分开”③。石文举例中即有“寝、寐、觉”一例。
研究者多以动词为例,并得出汉语词汇发展中存在着从综合到分析的变化。这些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观察分析无疑是正确而富有启发性的。本文则试图从词汇类聚的角度来研究观察此类语言现象,以探求系统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制约。
语素类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同类词的语素类化和同义词的语素类化。
(一)同类词的语素类化
同类词的语素类化是用附加类名的方式使词形具有类聚性,如“枝”、“干”、“梢”为同类词,后分别加“树”,变成“树枝”、“树干”、“树梢”。
我们再举几例来说明:
第一组:和“脚”有关的名词——指(趾)、跖、跗、踵、踝
“趾”从字形来源上说是“止”的分化字。“止”本为象形字,象脚之形,《说文·止部》“止”字段注:“止为人足之称,许书无趾字,止即趾也。”“趾”在先秦并无“脚趾”义,而是指“足、脚”之义。如: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毛传:“四之日,周四月也,民无不举足而耕矣。”(《诗·豳风·七月》)
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因此,“趾”常以“足”作训。如:
有目有趾者。(《庄子·田子方》)成玄英疏:“趾,足也。”
天王亲趋玉趾。(《国语·吴语》)韦昭注:“趾,足也。”
在先秦两汉,无论“脚趾”、“手指”,一般均以“指”表示。如:
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左传·定公十四年》)杜预注:“其足大指见斩,遂失屦,姑浮取之。”
名曰鹦鹉。(《山海经·西山经》)郭璞注:“脚指前后各两扶南徼。”郝懿行《笺疏》中认为“指”作“趾”。
“跖”,《说文·足部》:“足下也。”段注:“跖,今所谓脚掌也。”
上峥山,踰深溪,跖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战国策·楚策一》)鲍彪注:“跖,足下。”
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也,必食其跖数千而后足。(《吕氏春秋·用众》)高诱注:“跖,鸡足踵。”
“跗”在先秦文献中,指“脚背”。例如:
乃屦,綦结于跗。(《仪礼·士丧礼》)郑玄注:“跗,谓在足背之上。”
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庄子·秋水》)成玄英注:“跗,脚趺也。”
“踵”在先秦文献中,指“脚后跟”。例如:
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荀子·荣辱》)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战国策·赵策》)
把这些和“脚”有关的意义古今表达形式对比如下:
指(趾)——脚趾
跗——脚面
跖——脚掌
踵——脚跟
踝——脚脖
这是一组比较典型的语素类化。
第二组:表示和“腿”有关的词——股、胫、腓
在先秦文献中,这些词都可以独立运用。如:
(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战国策·秦策一》)
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胫。(《论语·宪问》)
六二,咸其腓,凶。(《易·成》)朱熹《本义》:“腓,足肚也。”
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庄子·天下》)
其中,“股”为“大腿”,“胫”为“小腿”,“腓”为“腿肚”。合成造词阶段,这些单位分别在词形上进行调整,以“腿”作为相同的语素延展开来。
更能够体现聚合形式有序性变化的是语素累增的类型。例如:
第三组:表示“花”部位的词——萼、蕊
在先秦文献中,“萼”、“蕊”可以独立运用。如: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诗·小雅·常棣》)郑玄笺:“承华者曰鄂。”
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楚辞·离骚》)
“鄂”与“萼”同,表示“花萼”。在合成阶段,“萼”、“蕊”分别用“花萼”、“花蕊”表示,词义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花”并没有对词义起到任何的改变作用。从个体词的形式表达来说,这种累增似乎对词没有什么作用,但从词汇系统的内部来说,语素的累增则是系统有序性的调整,从而和“花瓣”、“花心”、“花房”形成对应。
诸如“骏马”、“树枝”、“门扉”、“羊羔”、“牛犊”以及“柳树”、“杨树”、“鲤鱼”、“鳟鱼”、“鲩鱼”等均属于此类变化。
(二)同义词的语素类化
同义词的语素类化常常由一个义域较宽的词以自身或自身的组合取代聚合中的其他词。例如:
第一组:视觉词
《说文》中表示“看”这一动作的词共100例左右。从训释的结构来说,既包括义界也包括直训。我们知道,在专书训释中,直训和义界所反映的均为被训释词的概括意义。“直训一般以同义词或类词为训;义界中主训词选取的为被训释词的上位词或同义词。”④王宁先生指出优化的义界原则之一为主训词与被训词的临近原则。
《说文》在对“视觉词”的训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训释词为“视”,共64次;其中“视”出现在义界中60次,出现在直训中4次。例如:
睨,斜视也
睼,迎视也
瞻,临视也
瞀,氐目谨视也
,小视也
睗,目疾视也
从义素分析的角度,如果把以“视”为训的这些词作为一个小的聚合的话,那么,这个义场中所有成员的共有语义成分就是“视”的整体词义,可以说,“视”为“睨”、“睼”、“瞻”、“瞀”、“ ”、“睗”等词的上位词,义域较为宽泛。这也能够说明“视”在这个聚合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词汇系统中的常用性。因为从训释原理上看,训释词常为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这样才能达到训释的目的。“视”在词义上的特征使它能够通过自身的分化表达其他词所能表达的概念。如:
直视= 、眙
原来用单音词表达的语义绝大多数可以用“动作状态 视”来表达,也就是说,相同的意义在古今汉语采用了不同的表达形式。作为个体来讲,前者用单音词表示,后者则用复合词或短语来分解其整体意义,词语的形式对意义的体现具有分析性。作为聚合整体来说,则是“视”在词形上对其他词的类化作用,使整个聚合场在词形上趋同。
第二组:“沐浴”类——沐、浴、沬、澡、盥、洗
《说文》对这些词的训释为:“沐,濯发也”、“浴,洒身也”、“沫,洒面也”、“澡,洒手也”、“盥,澡手也”、“洗,洒足也”。
再来看这些词的文献用例:
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能去一形之垢,其实等也。(汉·王充《论衡·讥日》)
故《顾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颜师古注:“沫,洗面也……沬即额字也。”(《汉书·律历志下》)
士盥,举鼎,主人先入。(《仪礼·少牢馈食礼》)
儒有澡身而浴德。(《礼记·儒行》)
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请靧;足垢,燂汤请洗。(《礼记·内则》)
从《说文》训释和文献用例可以看出,古汉语中这组词的差别在于受事对象的不同。沐、浴、沫、澡、盥、洗的受事对象分别是头、身体、面部、手、脚。发展到现代汉语,“洗”仍然作为词使用,而其他的词则失去了独立性,它们所表达的语义也完全可以以“洗”的组合来表达。
沐=洗头、盥=洗手、洗(本义)=洗脚、沫=洗脸
第三组:行走类
《说文》中,表示“行走”的词共40个左右,在训释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为“行”,共27例。如:
赹,独行也
趛,低头疾行也
,直行也
,轻行也
趚,侧行也
和“视”相同,说明“行”在这个聚合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词汇系统中的常用性,这是“行”在词义上分化的前提。发展到现代汉语,“行”仍然作为较为活跃的构词语素使用,而其他的词则多数失去了自由组合的能力,它们所表达的语义也完全可以以“行”的组合来表达。如“独行”、“疾行”、“直行”、“轻行”、“侧行”。
同义词的语素类化常伴随着语义场中某个词的词义泛化,即词在使用过程中表义的抽象化以及义域的扩大化。例如:“洗”本专指“洗足”,随着受事对象的逐渐扩大,表义变得抽象,泛指“清洗”。词义泛化是通过自身表义的抽象化来扩大义域的范围,属于演绎性的变化;语素类化则是一个义域宽泛的词取代同义词或是类名附加的过程,属于归纳性的变化。两者在词汇系统发展中相辅相成、互为前提。词义泛化和语素类化是汉语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现象,并非是哪个阶段所特有的,但在汉语从单音词向双音词过渡变化的过程中,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普遍。
我们认为,单音词系统在发展过程中语素类化的强势作用是汉语从派生阶段到合成阶段的词汇系统变化调整的必然结果。以下从几个方面说明:
第一,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改变
从组合关系来看,由于派生造词阶段词汇系统中以单音词为主,词内的组合关系基本是不存在的。发展到合成造词阶段,词的双音化带来了词内的组合关系的普遍性。如果说,派生造词阶段词汇系统中的最小元素是单音词,而在合成造词阶段词汇系统中的最小元素则是构词语素。由于组合关系和组合层次的变化,使得词汇系统的聚合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
索绪尔认为“由心理构成的集合并不限于把呈现某种共同点的要素拉在一起,心理还抓住在每个场合把要素联系在一起的种种关系的性质,从而有多少种关系,就造成多少个联想系列”⑤,因此在同一个聚合场中的成员必定在某一方面有着共同性。具体的聚合系列,“有时是形式和意义都有共同性,有时是只有形式或意义有共同性”⑥。对于词汇系统的研究来说,能够在聚合中找到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从形式与意义的规律性对应中,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词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和制约。
派生造词阶段,孳乳造字和派生造词的同步进行,使汉字的字形和它所记录的词的意义发生相对密切的关联,形、音、义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
第二,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改变是系统向有序性发展的调整
语言的本质是符号系统,内部可分为能指系统和所指系统,前者为形式,后者为意义。一个好的符号系统就在于能指系统是否能更有效地体现所指系统,体现越完善,符号系统的整体运转就越灵活有效。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比较中,我们会看到合成构词的优势不仅体现在能产性和区别力的加强,最为重要的是形式系统能够更有效地体现意义系统的差异和关联。
徐通锵曾指出汉语从单音词到复音词的变化是编码原则的变化,并认为单音词在编码原则上具有平行性,“就是各类名物性的现象在编码体系上都呈现出具体、明确、细致、离散,每个字都有确切的语义范围”⑦,“随着语言的发展,人们后来比较关注的是字义之间的横向联系”⑧。尽管徐先生在“字”的概念运用上存在问题并受到了较多质疑,但不能否认其在汉语词形与意义系统协调性上的敏锐观察。他指出汉语在发展中“把类、象合一的编码方式改为类、象分离,一字一类(或一象),用字组来实现编码的要求”⑨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这些观点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那就是作为一个自我运转的系统如何发展新的要素。除了在语言初期的原生阶段,语言中新要素的产生一定是在旧有要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旧有要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即为理据性的体现。派生造词阶段是以词所反映的物象特征作为新词与旧词之间的节点,这种物象特征的归纳便成为词的词源意义;合成阶段则多数是以语素的组合产生新词,新词与词汇系统的关联已经进入到词汇意义之中。正因为如此,派生阶段词与词之间能够在语言内部形式上体现出来的聚合是词源意义的聚合,词汇意义的聚合则只能寻求语言外部形式——文字,用文字的义符来体现词汇意义的某些关联,这种体现又是相对模糊和含混的。而合成阶段词与词之间完全可以从语言内部形式——语音上体现词汇意义的聚合。所以派生阶段词与词之间在形式上常常是离散的、孤立的、无序的;合成阶段则是关联的、有序的。从这一点上说,合成造词取代派生造词是汉语作为符号系统自我完善的选择。
这种调整不仅包括给新产生的意义赋予新的词形,同样也表现在对旧有意义的词形上的改造,使原有的离散形式凝聚成有序的关联。故而,我们就能够从汉语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提示的特征上来解释上述古今语义表达的类化性倾向。
我们再来看和“脚”有关的一组用例:
派生阶段:趾、跖、趺、踵、踝——形式聚合标志为义符“足”
合成阶段:脚趾、脚掌、脚面、脚跟、脚踝——形式聚合标志为内部语素“脚”
从意义来看,这几个词的限定性义素相同,关联点在于“和脚部相关”。在派生阶段,几个词在语言内部形式上不具有关联性,它们的关联只能从语言的外部形式——文字中观察到,即均以“足”作为义符。合成阶段,这一组词在词形上具有了相同的聚合标志——“脚”,它们分别以“脚”作为限定性成分进行了内部的分化——脚面、脚跟、脚趾、脚脖,语义的关联在形式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见,派生阶段词汇形式是独立的、个体的,合成阶段词汇形式则是整体的、关联的。
“沐浴”类的变化也是如此。
派生阶段:沐、浴、沫、盥、洗——形式聚合标志为义符“水”
合成阶段:洗头、洗身、洗脸、洗手、洗脚——形式聚合标志为内部语素“洗”
从意义上说,这组词有共同的意义成分——“使……变得清洁”。派生阶段,这个语义特征无法从词形上得到反映。合成阶段,大凡表示“使……清洁”的意义,均以“洗 对象”表示。这种表现形式实际上是将同义或同类聚合中的共同性要素提取并以外化的词形体现出来,使同义或同类的聚合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类推性和有序性。
第三,派生阶段词间关系的离散性与其造词特点相关
在派生阶段,词的最初来源常是依托于具体事物。尤其是动词、形容词的产生,动作和特征作用于不同的事物,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作出命名,词义内涵常是丰富的、具体的。“性状作为一种独立的编码对象在汉语的早期还没有分离出来。它寄托于名物,在编码的时候大体上都是通过某一类名物的摹写来衬托某种特定的性状。”⑩“汉语早期表示动作的一些字大多与特定的名物相联系,使它们只适用于一些特定种类的名物。”(11)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来看,动作、性状在依托上存在着等级的差别,即动作常依附于名物,而性状则对动作和名物均有依附。例如:
古汉语中和“红”相关的词有“赤”、“朱”、“丹”、“赭”。“赤”来源于火焰的颜色,《说文》:“赤,南方色也。”南方主火,故曰南方色。“朱”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认为来源于朱砂的颜色(12);一认为与“赤心木”有关。“丹”本指“丹砂”,《管子·地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后作为颜色也指像丹砂的颜色。“赭”,《说文》:“赤土也。”“‘赭土’可以用来染布帛,‘赭’染之布做的衣服称作‘赭衣’。”可见,这些颜色均依附于具体的事物,它们所表示的性状具有特指性。
“芳”、“香”也有类似的现象。宋玉《风赋》:“回穴冲陵,萧条众芳。”《楚辞·离骚》:“苟余情其信芳。”洪兴祖补注:“芳,香草也。”可见“芳”既可以指“香草”,又指“草香”。“香”在先秦汉语中,有一个意义密切关联的词——“皀”。《说文》:“皀,谷之馨香也。象嘉谷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说皀,一粒也。凡皀之属皆从皀。又读若香。”从“皀”的又音看和“香”读音相同,在意义上两者相关联,应具有同源关系。“香”为“黍稷香”,“皀”为“馨香的黍稷”。
当专指意义淡化后,就会导致一批词义略有差异的同义词产生,这是抽象特征从具体事物脱离后的殊途同归。“香”、“芳”的差异性淡化,同义性增强;前文中的“沐”、“浴”等词的变化也是如此,排除了具体的受事对象,它们的词义就变得相近。随着同义词之间差异性的减少和淡化,它们在使用中的价值也开始逐同。价值相同的要素必然会存在竞争,因此,总有一些要素在竞争中被取代,从而退出句法层面。
正是因为派生阶段造词的这种依附性,使很多先秦的单音词常能和现代汉语中的复合词及短语来对应。因此,这种变化从个体词来说的确是从“综合”到“分析”的变化,但如果放在系统中考察则是词汇从派生阶段到合成阶段词汇系统发展的必然结果。
①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全集》(第一集),第3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第228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③石毓智《古今汉语动词概念化方式的变化及其对语法的影响》,《汉语学习》2003年第5期,第1页。
④王宁《单语词典释义的性质与训诂释义方式的继承》,《中国语文》2002年第4期,第310页。
⑤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7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⑦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第33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⑧同上书,第335页。
⑨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第359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⑩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第33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同上。
(12)王凤阳《古辞辨》,第91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