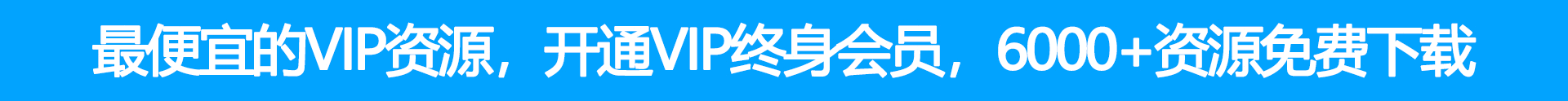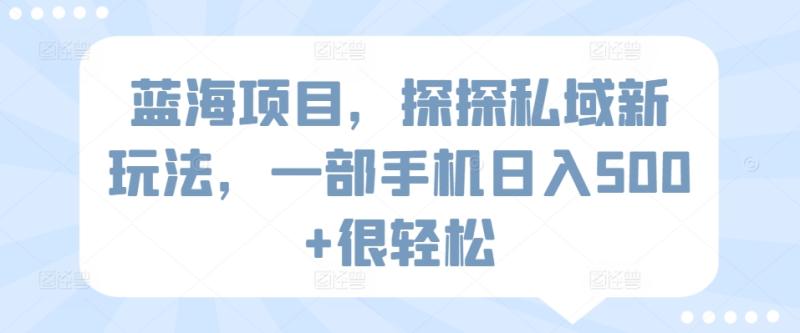那一段火热的乡村生活——打麦场上
——溪流 .2022.1 .
我出身农村。儿时的农村还处于建国初期,生活虽然不富裕,却充满活力。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农村的打麦场上,当年那种繁忙、火热、有趣的往事,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六月的宁夏川区开镰割麦,是“龙口夺食”的季节。从收割到打麦,全部是强体力劳动,社员们无不是头顶烈日,挥汗如雨,争分夺秒地和时间赛跑,和老天爷抢粮食。他们经历过那几年雨水多,麦子来不及上场,已经在地里发芽的事。丰收在即,谁也不想在这个档口功亏一篑,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当然,过去和现在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田间操作全部机械化,收割机“轰隆隆”一响,连收带打,杆、粒分离,直接拉回家了。只要把握好天气预报,“龙口夺食”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分量。
五~六十年代农村实行人民公社,每个生产队都有打麦场。我家在贺兰县常信公社新华五队,全队男女老少200来口人。耕种4~500亩土地,其中小麦大约超过300亩。那时候的小麦亩产不高,也就300斤左右。打麦场在李家庄子北面,离生产队的饲养圈不远,住家农户恰巧分布在场的南北两面,处于住家农户相对较近,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段。从春耕播种起,队长就规划好了麦场的位置,种植比小麦早熟几天的大麦。接着就是大麦开镰、灌水、压实、铲场、盖房,麦场启用。随后小麦开镰,一车一车的麦捆拉上场,麦场四周耸立起比房子还高的麦垛,把麦场围了一个圈。
开始打麦了,全队的劳动力几乎都集中到打麦场上,就连中、小学校也在这个时候放了假,学生娃们也掺和进来,麦场成了最繁忙、也是最热闹的地方。“打麦”也叫“打场”,实际是脱粒入库。基本工序是摊场,即打开麦捆,先把麦子均匀的铺在场面上晒干;压场,也叫碾场。即两匹牲口拉一个大石磙子,10多个磙子排成一队,转着圈反复碾压脱粒;翻场。把碾压到一定火候的麦子翻到另一面继续碾压脱粒;收场。即抖掉麦粒、收起麦杆,将已经脱离的麦粒拢成堆,利用风力飏去麦芒皮屑,即可装袋入库了。
300多亩的小麦怎么着也得忙活一个来月。打场这么重要的工作,无疑全靠生产队长的合理调度。但是怎样才能“好钢用在刀刃上”、既不窝工又不费时,这就要看生产队长的组织能力了。我们队有三个队长: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妇女队长。政治队长是谁,想不起来了。生产队长李学忠、妇女队长朱金兰却记得清清楚楚。他们俩人当时30郎当岁,一个孔武有力,一个风姿绰约,正是青春好年华。打场这个活既繁忙又繁琐,有间断有连接,有分工有合作。看起来繁杂混乱的工作,都被我们队长安排得周到妥贴,井井有条。李队长全面调度,朱队长场上具体负责,打场就这么井然有序的进行着。一般情况下,男的套牲口赶磙子,女的翻场。年龄大的壮劳力飏场,收场时男女社员一块上。放假参加劳动的大一些的学生娃娃,男孩子也有赶磙子的,女孩子也有翻场的。我那时候12~3岁,队长也让我和另外两个男孩“赶磙子”,不过只能是“驴磙子”。套磙子一般都是双牲口,即两匹马或骡子,亦或两头驴。能让我赶驴磙子已经相当不错了。驴相比骡马个头儿小,比较温顺、听话,容易驾驭。找几个孩子赶“驴磙子”,弥补了壮劳力的不足,这让我感到庆幸,也让其他类似我这样的半大孩子们羡慕不已。
队长李学忠一家是我们队的大户人家。父辈是老哥仨,哥仨又个个人丁兴旺、儿女满堂。李学忠是长房长子,三兄弟三姐妹。两个弟弟一个是矿山上的干部,一个是县上的干部。在我们这一块儿,一家一户的庄户人家,有院没院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几间土坯房,稀稀拉拉的分布在一条东西向土路的两侧,这是一条连接公社西面于祥、五渠大队的路。唯有路南的李家庄子高墙大院,树木簇拥,在周围一户一户的农家小院中,鹤立鸡群般格外显眼。远远望去,像一座城堡。那时候老弟兄仨都住在院里。李家是土夯的大院,院墙差不多和屋顶持平,大门开在东面,院墙周围除了柏树、柳树、榆树外,还有果树和桑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爬上他家的桑树摘桑仁吃,嘴巴黑紫黑紫的。说到队长李学忠,社员们都会伸出大拇哥,异口同声地赞叹:是个好队长。小伙子1米8的个儿,大眼睛阔嘴巴,长的虎虎生气。别看年龄不大,论起种田却是经验老道,一点不输旁人。那是他有一个庄稼“把式”的父亲耳提面授的结果。李队长有个绝活:鞭子抡得响,马车赶得好。队里有两挂马车。收麦上场的时候,马车上的麦捆装得像小山一样,没有路的庄稼地里沟沟坎坎、凹凸不平,弄不好就会陷在坑里赶不上来。每当这时候,就会喊来李学忠。只见他抡起鞭子,先“啪、啪”两鞭抽在地上,鞭炮般的声音在耳边炸响。抡起的鞭子在空中划着圈,却不落在马身上。无论是辕马还是稍马立刻来了精神,有的还纵身跳了起来。李队长一声吆喝,三匹马弓起腰、蹦紧腿,鼻孔喷着长气,崩直的车套像要断开一样,马车随着晃动出了泥坑。看来,即便是赶马车,气势和技巧一样都不能少。这个世界上就这么不一样:你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你办不好的事他能办好。
李队长这个人的性格有点“二”,但也不失“暖”。他媳妇生孩子一天一夜生不下来,疼的得哭爹喊娘。队上的接生婆不行,又找来医生,还是不行,一家人束手无策。李学忠急了,一步跨到炕上,抱起媳妇的后腰,往上一提,孩子“哗啦”一下出来了,一声嘹亮的啼哭和一阵惊叹声响起。这么个性命攸关的大难题被他这么一“二”解决了!如果不“二”呢?不堪设想。队里每年的新麦下来前都有几天青黄不接的日子,家家户户的旧粮和新麦接续不上,谁家都为这几天断粮发愁。李队长也干了件违反政策的事。他让每家出一个人,集中到生产队上的麦地里捋麦穗。大队干部们看见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搓净的麦粒煮着吃,几天的饥荒就这么过去了。设想他如果坚持原则不这么办呢?同样合情合理。毫无疑问,他是为全队的社员们担着风险呐!
火一样的日头挂在天上,风不吹树不摇。稍远处湖边的青蛙“呱、呱”地叫着,脚边的草叶子都蔫了下来。麦场上十几对牲口、十几个石磙子排着队,不紧不慢地在麦秸杆上转着圈。只有赶着头磙的王老五戴着草帽,穿着无领无袖的白衬衫,嘴里振振有词的吼着秦腔,手里的鞭子有起有落的给自己打着节拍。后面的“赶磙人”有气无力的跟成一行,不时传来一、两句简短的吆喝声。我们队的老一辈中有两个大个子。一个是李学忠的二爹,即二叔,再一个就是王老五了。说什么也超过1米8吧?王老五是弟兄排行第五,平辈人都叫他王老五,或者王大个子。小辈人都叫他“王姨爹”。在我们这一块儿,对辈分、年龄大的邻居统称“姨爹”、“姨妈”,前面冠姓即可。北方的外地人好像“张叔”、“李婶”的那么称呼。王老五的大名叫什么,别说我们小辈人不知道,他们平辈人恐怕也没几个人知道。王老五叫的顺嘴,真名就撂到脑后了。王老五人缘好,爱热闹,走到哪里都是笑声一片。我第一次赶磙子有点紧张,尽管处处小心翼翼,但是怎么套磙,怎么使驴,还是手足无措,只能“傻子过年看邻居”了。好在这也不是什么高科技。我先看着人家怎么干,再自己模仿,加上旁边大人不时地指导,这“第一次”就这么过来了。当我牵着驴缰绳,赶着“驴磙子”融入到队伍的行列中,在旁边随行时,心里不由得“小得意”:不过如此嘛,没什么了不起!一边听王老五吼秦腔,一边胡乱揣摩唱词里的情节,最终只觉得王老五摇头晃脑、抑扬顿挫的样子滑稽可笑,吼得有趣。至于唱得什么内容,云里雾里的不知所云。
场房屋檐下、麦垛边的阴凉处,坐着等待翻场的妇女们。她们有的摇着草帽扇风,有的闷头纳着鞋底,有的几个人窃窃私语,有的围成一团说着家长里短,不时传来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还有和王老五年龄相仿的婆姨大声叫着:“老五,声音再大点”!旁边的人也跟着起哄,笑声中王老五吼得更起劲了。这个王老五可不是一般人。别看他没什么文化,却有一肚子故事。什么《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说起来声情并茂,一套一套的。他诙谐、幽默,总会因人因事,有感而发地讲个典故,说个笑话。闲暇之余,或者聚拢干活时,比如插秧、薅稻子的时候,大家都紧着往他身边凑,边干活边听他说书。他又善于在故事的裉节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故意吊人们的胃口。搞得大家五迷三道的惦记上了。在那个年代,农村人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不像现在有电视、手机,广场舞、健身操的,一般也就是看看露天电影,听听有线广播。听人说书,是农村人的日常消遣。王老五,那可是我们队上大家非常喜欢的人。提起王老五,想起一件趣事。这个人爱串门,爱和人“谝闲传”,拉起呱来没完没了,家里吃饭经常不见人。他老婆常常拉着小女儿找他。小女儿名叫兰兰。找老头时她不叫王老五,也不叫他的大名,而是亮开嗓门、拉长声调,嘴里喊着小女儿的名字:“啁——,兰兰!——”。而兰兰则是支楞着耳朵听着妈妈叫着自己,站在一旁选择一声不吭,好像兰兰与她毫不相干。母女俩如此默契,我想她肯定知道妈妈为什么会“骑着马找马“,因为兰兰知道那是在叫爸爸而不是叫她。
人们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点不假。小时候听她们讲的事至今还有记忆。比如队里的小伙子张占雄的哥哥,在石炭井出工伤死了,张占雄娶了嫂子接了班当了工人;常信小学的汪主任媳妇难产死了又娶了小姨子;从银川下放到队上那家姓任的女儿找了个煤矿工人。其实,她们说的这些事一点不虚,都是真的。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农民对工作、对工人、城里人的向往就摆在那里,无论他们做出什么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
打麦场上还有一件大人们高兴、小孩们企盼的事。那时候我们生产队有几亩瓜、菜地,种着西瓜、小香瓜,和一些辣椒、茄子、西红柿之类的蔬菜。由于当时没有自留地,也没有农村集市。社员们各家各户日常吃的的蔬菜就由队里自己解决,价格便宜,不用付现款,取菜记账,年底统一结算。西瓜和香瓜一部分分给社员,一部分偷偷的拉出去,走家转户的卖掉,给生产队增加些收入。自由买卖在当时是不允许的,也没有集贸市场。一个队里几百口人的生活用度,生产队长都要想办法顾及。七、八月的天热的人头晕,一动一身汗。队长李学忠派人把西瓜、香瓜送到场上,磙子也停了下来,男女老少一块吃瓜。大人笑、孩子叫,热闹极了。
记得当时负责瓜菜地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姓乔的老汉,他是我们队上的能人。会榨油,会磨豆腐,会种菜。人们都叫他“乔油匠”。一般情况下,进入腊月,队里才安排他榨几天油,磨几天豆腐,分给社员过年。在种菜上,我依稀记得他说的几句话:“梅豆干,辣椒泥,茄子沟里能养鱼”。意思是豆角浇水不多,辣椒和茄子喜欢潮湿,益于生长。说起“过光景”,乔油匠在我们队里能算上等。他家三口人,两个劳力,一个女儿。人口少,吃闲饭的少,生活自然差不了。记得他老婆叫龙玉凤,是个接生婆。经常给人接生,挣些“外块”,小日子过得比一般社员滋润多了。他女儿乔月兰和我一个学校,比我年长些,人长得精神,身材苗条,乌黑的头发,两条小辫,高鼻梁、大眼睛,能歌善舞,是我们公社的文娱骨干。每年公社组织文艺宣传队都少不了她。记得她和一个叫陆山的,演的藏族舞蹈《逛新城》,那是一个“好”字了得。二人藏族服装一穿,陆山的两撇胡子插在鼻孔里,音乐响起,女的轻快飘逸,男的诙谐滑稽,且歌且舞,珠联璧合,台下一片掌声。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农村的女孩子几乎都是扎小辫。短散发、马尾辫也很少见。至于什么长发披肩、不男不女、染成各种颜色的发型更是没有见过
下午时分,狂风骤起,西边聚起乌云,雷声隆隆,眨眼间涌上头顶。妇女队长朱金兰眼看大雨将至,一边招呼停下磙子,一边叫大家赶快起场。这时候也不分什么活该男人干还是女人干了,捞起什么工具就干什么活,什么急就先干什么。抖开麦桔抬到场边,把脱下的麦粒连皮带屑拢成几个大堆,拉来苫布盖严实。说话间天黑了下来,雷声接连在头顶炸响,一道一道的闪电晃得人睁不开眼,大雨点落了下来,打在苫布上噼啪乱响。还好赶在雨前收拾停当。大家拿起工具,跑进场房,门前、窗前挤成一团,眼看着雨点变成雨团,周围涌起的霧汽迷迷茫茫,十几米外什么也看不清楚,地上的水层越积越厚,甚至能听到附近“簌簌“的流水声。一阵紧张激烈的忙活,身上的汗热还未散去。大家庆幸朱金兰指挥得当,庆幸全场小麦未遭损失。不过也有风急雨骤来不及起场、小麦泡在雨水里的时候,这样麻烦就大了。小麦只能晒了又晒,一道一道的工序做了再做,费时费力不说,尤其质量下降不少。由此可见恰当的指挥有多重要。
夜晚看场是打麦场上的重要环节。可惜我先是年龄小轮不上,往后则是上学、当兵离开生产队,再没有亲身体验的机会了。麦场上有一块刻着《天下太平》的长条形木牌。每晚下工前,队长都会当着接班人员的面,把《天下太平》的印记加盖在麦堆四周,第二天经查验后,确认堆型、印记无误,没有任何改变方可交班。看场是两人一组。不能一家人,也不能男女同班,以防“瓜田李下”说不清楚。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当时队上一个姓赵、一个姓张的正在谈恋爱的小年轻要求一块看场,想让李队长成全他们一次机会。尽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是队长还是不允许。据我所知,我们生产队的麦场上从没有发生过被盗、火灾、水灾等责任事故。尽管六~七十年代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给苏联还债,我们宁夏人民同样忍饥挨饿、生活困难,但我们队的社员没有一个人向国家、向集体伸出“三支手”。那个年代的民风淳朴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