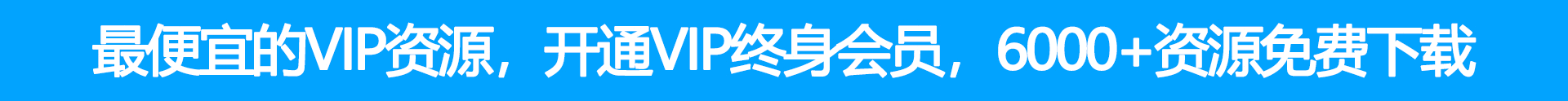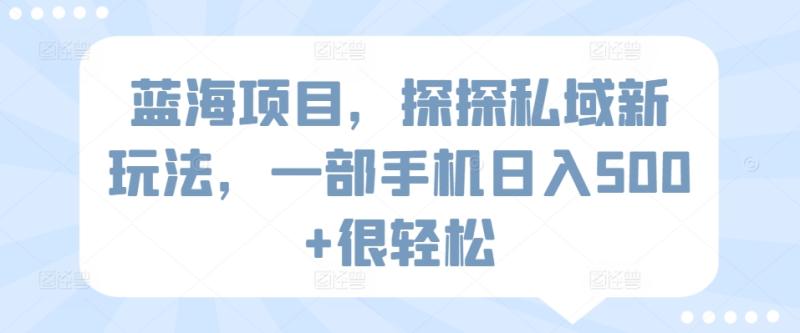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作者:寻访中国第一代农民工
本文系刺猬公社X快手“还乡手记”非虚构故事大赛参选作品,王磊光为2015年春节期间刷屏文章《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作者。
作者 | 王磊光
不是开始的开始
2011年,农民工朱建民带着妻儿回家过年。
没有回家,已经十三年了!车驶入大别山,山水越来越熟悉,他泪流满面。
“十三年变化多大呀!当初五十多岁的人,很多都已经不在了。同辈中,很多人也都已经老了。”
十三年间主要是通过电话跟亲人联系,同四哥朱七一的联系最为紧密。虽然后来可以网上视频,但他不喜欢视频。也许,他无法面对亲人吧。
“回来的第一感受就是对不起亲人。十三年不回,肯定是对不起啊!”说到这里,朱建民再次啜泣起来。“最开始只是有一个发财的梦想,没有发财便十三年不回老家,好残忍啊!即使没有钱,每年都应该回来看看。”
是啊,要发财与要回家,从来都不是矛盾的。难道是有什么更隐秘的原因,让朱建民无法面对家乡?我有一位朋友,同样是在外打拼,迄今已15年没有回家了。家里的老房子,是依然在风雨中飘摇,还是已经倒掉,他都不知道。他不回家,不仅仅是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来逼迫自己在城市里闯出一条血路,更是因为他始终无法面对少年时代的贫穷和被剥夺带来的耻辱感——他成长的年代正是农民税费负担最沉重的年代,为了收税,村干部连家里的一只热水瓶都提走了。
在朱建民内心深处,大约也有一份无法直面的痛楚吧?
回到家,他们继续住在几十年前的老屋里。老屋一直由哑巴大哥照管,才保存完好。
物是人非、人生如梦,发财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平安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朱建民回到家乡时得到的最深刻的领悟。
此后几年,朱建民每年都会带着妻儿回家过年,到一些亲戚家走动走动。
但有一家亲戚,他一直没有去。那是他的嫡亲表哥家。表哥是从L县走出的杰出人才,据说现在身家已经上百亿,是商界的风云人物。
2017年腊月二十二,坐在我面前泪眼模糊的朱建民对我说:“表哥家早已没有人居住了。但我昨天还是开车去了他家,在大门的对面望了半个小时,只是望着,没有进去。他家已经建成了别墅,有三个人在搞装修,不知道今年过年有没有人回来……”
表哥名校毕业,刚走上社会就占据重要舞台;而朱建民第一次闯入社会,便是流落街头。这中间的差距,他不是不明白。表哥早已是朱建民永远遥不可及的梦想。
1998—2017:朱建民自述
“1998年,我刚到浙江,找不到工作,就去当渔民, 600块钱一个月。在船上没有怎么吃饭,却一直吐,最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实在是太苦了。我对比我年纪还小的小兄弟说:不要在船上做事,没有前途,要去岸上找一份工作。其实,这何尝不是我对我自己的劝说!在海上我们打到的唯一的鱼,是一条八米长的大鲨鱼,当时网都拉不动。我只干了一个月,就辞职了。我要去岸上寻找属于我的大鲨鱼。
“上岸后找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机械厂。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厂。应聘的时候,我对老板说:我可以把这个机械的原理都弄懂,然后帮你跑全国的销售。所以我在厂里学做装配工。所谓装配工,就是要从零件到机械成型都要懂,是一个比较有技术的工作。装配工需要三年出师,但我对许诺一年可以出师。我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努力,只要付出得多,肯定可以提前出师。在这一年当中,我仔细钻研,不懂就问,因为装配工必须要懂得车床、钻床,甚至磨床,是比较综合的一个工种。最开始连游标、卡尺都读不懂,但最后,机械的安装、操作、运行,我都掌握了。一年之后,我真的出了师。
“在这一年中,发生了很多故事,比如我把我的老乡介绍了进去,在里面打杂。老乡年龄比较大,头脑没有我灵活。他进去打杂,五六百块一个月,我当学徒工,三百块一个月,但几个月后,我也拿到了五六百一个月,出师后就会拿更多。老板跟我年纪差不多,我会打乒乓球,经常跟老板一起打,我的字写得好,口才也好,老板很器重我。但有一天,老板突然对我说:你不适合做装配,让你的老乡做装配。我一头雾水:我这么努力,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做装配?我当即眼泪就流下来了。这样一来,我老乡去搞装配,换成我来打杂。打杂做什么呢?修车、扫地等。老乡年纪大,学起装配比较慢,几个月之后,老板还是让老乡继续打杂,让我重新回到了装配的位置上。当时我老婆在食堂帮忙,有五六百一个月。一年之后,我出了师,但是老板突然宣布把我开除。我当时听了,莫名其妙。我没有犯任何错误,掌握了技术,也非常努力,以后还可以帮他搞销售,但是老板突然宣布把我开除。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何故。我走了之后,我的老乡重新回到装配工的位置上,后来又回到打杂的位置上,十几年之后也成了百万富翁,打杂也成了百万富翁。我的运气非常差,打工没有赚到钱。每次快到巅峰的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99年的时候,我被一个朋友骗去广东做传销。每天除了听课,写信,发电报,就是睡觉。吃饭除了大白菜还是大白菜,几乎没有油,因为没有资金。哪怕买日用品,也都有几个人跟着。我没有深陷其中,想方设法逃了出来。那个骗我去的朋友年纪小,不懂事,容易上当,那时候已经被骗了上万元,那个年代,万元不是小数字,我劝他跟我一起离开,他不肯。最后我还是逃票回来的。”
“2001年,我进入了顺丰快递公司。当时我对快递行业完全没有概念,只是抱着尝试的想法做一做。从收派员做起,这是最末端的工作,相当于邮递员。那个年代手机使用的人还很少,我没有通讯工具,就买了一个BP机。BP机器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数字机,一种是中文机。我买了一个中文机,两三百块。快递行业是一种服务业,在做快递过程中,态度好、服务好,人家才会认同你。人家认同你,有收件自然会有寄件。顺丰快递1993年成立于广东,后来慢慢向省外发展,2001年的时候,T市的顺丰快递公司才成立不久,我成了第一批收派员,我的工号是002号,在我上班的第一天,001号辞职了,他看不到快递行业的未来。但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意味着一种机遇。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公司呢?在一个小区里租了一个门面,卷帘门。这就是公司的工作场所。楼上是办公的地方,有经理、文员、还有一个综合文员,还有一个是服务员——专门搞售后的。那个时候快递不准挂牌营业,因为邮政一家独大,三五天就会查一次,一旦被查出来,随时都要被关门。我们只能躲着营业,像做贼一样。那时候T市的快递也主要是寄送机器的零配件,因为T市是一个工业城市。而且人们对快递行业还普遍缺乏认识和信任,高端一点的东西,都是通过邮局来寄送。我们几个派送员,每个人负责一块。我花几十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靠这辆自行车把快件送到客户手中。客户觉得我的服务很好,慢慢地我的业务也就起来了,越做越大,后来在整个T市,我的业务排名第一,2001年最高的时候拿到了3500块钱一个月。
“我做了一年的收派员,就升任为主管。我经理是我的朋友,对我很信任。T市哪里的网点出了问题,他就把我派到哪里做到主管,解决问题。总共做了六年主管,一直做到2007年。但是主管的工资不一定强过收派员,主管最开始是拿固定工资,1500块钱一个月,后来通过考核,根据绩效来给工资。主管最高拿到的最高的工资是3800。我做主管时还被客户绑架过。客户从我们的网点寄了两票黄金到深圳,一票三十万,一票十九万,寄丢了。客户表示:我们不赔钱,就别想走人。客户把我的点封掉了,派几个人把我软禁在酒店里,陪我吃住,抽的是中华烟,就是不要我走。我手下有十几个人,我只好遥控指挥,到处打游击,办理快递的交接。就这样维持了几个月。但最终,公安局破了案,是广东那边的收派员监守自盗。
“做了主管,有希望升任运作主管。很多人都认为我是最有希望的。2005年,我们有四个人到温州去接受面试考核。最终的结果是,我只是一个储备运作主管,意思是没有正式录取,等到需要用的时候才可能用。另外一个人做了运作主管,成了我的领导。我继续当我的主管。我要是当了运作主管,我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如果我做了运作主管,我现在可以说是在开奥迪、奔驰。
“我的那个朋友后来又升了官,调到S市当区部人力资源部总监。调来了一个新经理。曾经跟我一起竞争运作主管的那个人,现在也是我的上司。我这人性格耿直,锋芒毕露,无论是经理还是运作主管,我都看不上,跟他们关系搞不好。于是我处处被穿小鞋,受刁难,遭受攻击。做得好得不到鼓励,做得不好那就更不用说。就这样,我在一怒之下就辞职了。我是含着眼泪写的辞职报告。这是2007年夏天。我辞职的时候,总部的人还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辞职。我的那个做人力总监的朋友让我去他那边,我也不去。我去意已定。
“从顺丰辞职后,我改行跑销售。从07年到2013年,我一直在跑业务,6年间换了三四家公司。我的业务是跑建筑材料,建筑材料都是针对大工程,不可能是小工程。于是这就需要关系。我一个外地人,虽然口才好,交际能力也不错,但是就是没有关系。我的一些朋友也都是在快递行业。跑业务是底薪加提成,底薪一般2500一个月。一年赚了个五到六万块钱。跑业务没有赚到钱。我还在一个生产汽车零配件的公司跑过销售。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面对同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忽然感到跑业务已经不太适合我了。在S市做人力总监的那个朋友,这时候已经调到了顺丰总部,跟在老总身边。我跟他说:我还是想回来。一般来说,年龄超过了35岁,顺丰就不收,但2013年,我已经43岁了。我重新回到了顺丰。回到顺丰还是做销售。顺丰不是搞快递吗,为什么也要做销售?有些大工厂一个月的快递费就要几万,有的淘宝店一个月的快递费要几十万。顺丰的销售主要是针对大客户,我们也有具体产品,产品就是快递。顺丰的销售其实就是维护客户,打开客户市场。我们的快递公司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合适的快递服务。说实话,做快递销售,我潇洒了几个月,工资一般在一万以上。我从13年做到15年,干了两年。这两年干得也算是可以,但是还是没有存下钱。为什么要辞职呢?因为在顺丰公司做事的主要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且如今的顺丰业务越做越大,风气也在迅速变化,不是从前的顺丰了。其中很多故事说来话长。总之是不愿同流合污,最后被人踢出,调到一个几乎没有业务的偏僻点跑销售,我又再次辞职。
“从01年到07年,从13年到15年,在顺丰前后干了十年。顺丰是我付出心血最多的地方,我对它怀着深厚的感情。(说至此,他的眼睛又湿润了。)顺丰的服务好,速度快,连邮电局的员工寄最贵的东西时,也都拿到顺丰来寄。
“从顺丰出来后,我又跑起了销售,先是在W市的一家激光切割机跑销售,又在N市的一家生产LED灯的公司跑销售,又发生了很多故事。又辞了职,到了17年,进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工作。保险公司说是底薪加提成,如果没有业绩,连底薪也没有。我进保险公司不后悔,起码让我了解了保险。
“我事业上虽然不成功,但妻子跟我在一起过了二十多年,对我始终是不离不弃,充满了鼓励。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对于儿子的教育,我很愧疚。儿子当过一年的留守儿童,孩子不在父母身边就要出问题。他初中毕业就没有再读书。他爱打台球,八岁时就在打台球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我送他去北京上斯诺克学院,成绩在学院排名第四。台球学院需要读三年,但终于因为无力支撑一年10万的费用,读了一年后,他只能选择让儿子退出。儿子因此变得不爱说话,不爱与人交流。为了培养他打球,我前后负债十几万,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还严重地打击了他的自信心。斯诺克是最难的体育运动,也是贵族项目,像我这样的经济条件不可能让儿子继续。
“我当时出去的时候,发过誓:没有发财,就不回家。我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十年。
从1998年一直到2011年,不仅是过年的时候没有回来,平时也没有回来,十三年无缝隙地未回。十三年过去了,我对自己说:十三年终于没有发财,但我也要回老家。”
不是过渡的过渡
原本,我是追踪朱建民四哥的故事去的。四哥朱七一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在外打工二十年;终于,他结束了打工生涯,回归家乡。一个人走得再远,还是要走回来的;一个人打工再久,终将还是要回到故土:这是第一代农民工对于生活的普遍认知。回乡后依然闲不住,朱七一做了一件吃力却不一定讨好的事——带领村民进行村庄环境治理,还集体出资数百万,建了游客接待中心,但由于政策限制和资金不足而陷入困顿,前景未卜。我曾将所见所闻截取一段,写成《水口实践》一文,发表于“澎湃新闻”。这篇文章在L县引起了极大关注,尤其是引发了当地父母官的思考和讨论。
在《水口实践》中,朱七一这样介绍自己:
“我是67年出生的。七岁时父亲过世,母亲是村里了不得的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几个拉扯大。我高中毕业,没有考取大学,就回来生产,然后外出打工。我在浙江的船上打过鱼,在新疆种过棉花,在工地上挑过砖,搅拌混泥土,还安装水电,搞消防……什么都干过。我读过书,比同代的一般人多点知识,但没有技术,打工收入就没有保障,除了能写会算,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打工之路非常艰辛。我在外面打工20年,去过全国三分之一的地方。在新疆,离边境只有十公里。打工的日子不好过。2010年回来后,就没有再出去。”对于20年的打工生活,朱七一的叙述是简略的,但其中的辛酸藏在他心中,大约不足为外人道。
原本,我是来追踪朱七一的故事的,却无意中收获了朱建民的故事。如果不是过年,我遇见不上他。这是我第四次来水口,住了两天半。前三次没有碰到水口塆的任何年轻人,因为他们全都在外打工,而朱建民,早不在年轻人之列,依然奔走在打工路上。
1970年出生的朱建民,是水口塆的第一个外出打工者,在水口塆所在的鸠鹚河镇,在鸠鹚河镇所在的L县,恐怕也都是最早的打工者之一。现在,水口塆仍在外打工的人员中,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个。
谈及这个弟弟,朱七一说:“要说打工,我非常坷坎,但我家老五比我还坷坎。”“坷坎”是L县的方言,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坎坷”,但从方言里表达出来,“坷坎”似乎比“坎坷”更有形象感,更带力度,更让人觉得刺痛。
改造前的水口塆。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供图
腊月底,年轻人一起吃烧烤,商量塆落整治。
1988—1990:到武汉去,到青岛去
“我打工不成功的原因,一是与我的文化程度有关,我是初中毕业,1987年初中毕的业;二是身体不好,我母亲怀我七个多月就把我生了下来,生下来的时候只有一两斤,而且母亲年纪大,没有母乳。读初中的时候,我修了一年的学,因为交不起学费。一期要交15块的费用。早餐店的油条,8分钱一根,买不起,真想吃啊,肚子老是饿的。因为没有钱,我休学了一年,挖药材卖,挖了一整个冬季的苍术。我给自己规定是一天挖两篮,一个冬季卖了150块,鸠鹚河镇价格低,就坐车到邻镇大河岸去卖。当时觉得150块真是巨富。”至今依然瘦弱的朱建民,让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他幼时先天不足、营养不良的窘迫境况,也让我们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必须得靠体力吃饭的农民工来说,身体不好又是多么大障碍。
当我问起这150块钱是怎么花的,他却早已记不得了,只是记得自己到了学校,手头有了钱,觉得日子极好过。
“我哥当时也因为没有钱,修了一年的学,他也在家里挣钱。他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又重新读书。”
但当我向朱七一求证休学一事时,朱七一说自己并没有休学,而是在1983年从农高毕业后开始做点小生意:从L县城拉饲料到镇里贩卖,赚了一点钱。
显然,朱建民的记忆是有误的。但他的讲述却印证了另一件事。——这还得回到我写的《水口实践》。文章是这样记录朱七一的讲述的:“我高中毕业,没有考取大学,就回来生产,然后外出打工。”其实,朱七一原本的讲述并非如此:他其实收到“华中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但不久后教育组来人,说是送错了,又把通知书收了回去。为什么当时我要把朱七一的讲述进行改动?因为事关公平与正义,极敏感,时间又过去那么久远,当时仅有当事人自己的讲述,我担心出现偏颇,便对叙述内容做了必要的处理。
朱建民讲起四哥的事情,依然充满激动:“通知书上写着‘华中农学院’和‘朱七一’几个字,我和邻居都看到了,哈哈大笑,说是考起了大学,就一起到河里去洗澡。哪晓得上面来人说通知书送错了,把通知书收了回去。那时候我们都不大懂,我哥十六岁,我十二三岁。这个事情永远是一个谜,到现在还是谜。你说,哪有通知书送错的情况?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朱七一的名字,永远都不会有通知书送错的情况!而且不可能同名吧?世界上还能找出几个叫朱七一的人?他当时只有十六七岁,说是送错了就送错了,没有把它当一回事。但是后来想起来心痛啊!这件事改变了我哥一生的命运。如果他那时候读了大学,命运就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跟着改变了:他考起了华中农学院,凭借他的才华和能力,没有县长一级的官,是打不住的,以后就可以关照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如此漂泊一生,也可能功成名就。”
1988年,18岁的朱建民同三个初中好友相约外出打工。其中一个伙伴说:我有亲戚在青岛上班,我们可以去投靠她。四个人中,最小的17岁,最大的19岁。他们把所有的钱都凑在了一起,有的凑了十块钱,有的凑了二十块,有的凑了几十块,然后开始了第一次打工之路。首先是要去县城,他们每人只买了一张去大河岸的票,却一直坐到了县城,短票长坐,是他们逃汽车票的办法;然后又坐汽车到了武汉,他们每人买了一张站台票,一直混到了青岛。
“哪晓得他的那个亲戚只是宾馆的服务员。一个宾馆服务员能有多大能力?她给我们管了一餐饭,就再也没有办法帮我们。我们在青岛混了几天,没有钱吃饭,看到地里有红薯就挖红薯吃,有萝卜就挖萝卜吃,就这样饱一餐饿一餐。没办法,只有回家。又是每人买了一张站台票,从青岛逃票到武汉。哪晓得到武汉要出站的时候出了事,我们四个人中有一个比较老实,看到检票员就非常紧张,缩头缩颈,检票的一把将他拦下。坏了,没有票!要补票又没有钱。检票员打开行李箱检查,看有什么值钱的。最后找到两副健身球,只有这个东西值点钱,拿去抵了车票。我们在青岛的时候,看到健身球极可爱,可以放在青石板上溜,就每个人偷了两副,带回来玩。那时候从青岛回来可能要十几块钱。我们就这样闯过去,又闯了回来。放在今天,今天的孩子想都不敢想。他们出去要把钱带足,要住好旅社。但是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理想。”
回忆起人生的第一次的闯荡,朱建民的言语间充满了欢乐,然而三十年前那种面临饥饿和居无定所时的那种无助,今天的年轻人又如何能够体会?
18岁的朱建民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次行动,让他已在无形中被历史放进了“第一代农民工”的行列。L县是大别山腹地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打工潮兴起之前,本地农民只能依赖种植粮食、板栗和养牲口来获取经济收入,打工潮兴起后,在外打工就成了农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查阅《L县志(1986–2005)》,关于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却只有寥寥几句话和一个数据缺失严重的表格:1986年,该县人口不足51万,开始有少量青年前往深圳、广州等地打工。1987年,该县人口不到52万,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有3890人。此后十多年,打工人口数量缺失,一直到2000年才有据可查,这一年,该县人口59万多,打工人数有61900人,此后五年,外出打工者急剧增加,到2005年,全县总人口依然是不足60万,但外出打工人数接近10万。
“第二次打工是在我19岁的时候,和张柏志去武汉找事。还算走运,我们在汽车站就被人找走了。是武汉长江电源厂招工,但招的不是正式工,而是厂房内部搞基建需要人手。我们在这里做杂工,15块钱一天,供吃,还有饮料喝。15块钱的工价在那个年代真是高。但正是大夏天,武汉又是火炉,我们没有宿舍,住在户外的工棚里,你想想有多热?夜晚根本睡不着。我睡在水龙头下,让水一直淋,还是睡不着。我们干了一天,住了一夜,实在受不了,就走路。直接回了家。
“第三次打工还是去武汉。我和另一个伙伴一起。哪晓得一出车站我们就走散了,我找不到他,他找不到我,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就想:既然来了,干脆就把武汉逛一圈。我反正会逃票,挤公交车把武汉三镇逛完了,还去看了黄鹤楼。”
青少年的这三段失败的打工经历,在朱建民看来,都是人生最开始的一些尝试,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打工。那么,这些尝试给了朱建民什么呢?我推测,应该是开阔了他的眼界,给予了他闯荡社会的勇气。
朱建民还记得,少年时代在家乡的大山里放牛,望着远处最高的那座山,想:“我将来一定要出这个界,到山的那一边去实现我的理想。”朱七一说:“我第一次去L县城是83年,参加高考。当时发洪水,月山庙那里的一座桥被冲断了,我从那里一直走到县城。”朱建民第一次去县城,比他哥要早,但也已经十余岁了。“车从家乡的盘山公路上转出来,眼前是一条大路,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宽这么直的路,我说:这路不需要掌方向盘。”
朱建民说的这座高山,就是鄂东名山薄刀锋。
1991—1995:在无锡
在朱建民看来,1991年去无锡当印花工,才是他真正打工的起点。这一年他21岁。
“江苏无锡有个丝绸印花厂,跟我们的大河岸镇有合作关系,大河岸有个缫丝厂,出售丝绸到这个厂,这个厂再将丝加工成布,印上花,出口到国外,利润非常高。后来这个厂来大河岸招工,当时我姐在大河岸镇工作,就给我报了名。于是一批L县人招到那个厂里工作。”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L县的蚕丝产量在1980年代达到湖北第一,各个乡镇都设有桑蚕收购站,可是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蚕桑业全面崩溃,缫丝厂也垮了,蚕丝几乎无人收购。蚕农们排着长队,一个个忍饥挨饿地向收购站的人说好话,就差没有向他们磕头祈求,任他们挑三拣四,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挑走没有一丁点瑕疵的那部分蚕丝——我还记得那一年母亲清早去镇上卖蚕丝,到天黑才回来,一季蚕丝卖了十多块钱。其状之惨烈,远超1932年茅盾在《春蚕》中所描述的景象。终于,全县农民充满仇恨地把桑树挖个干净。我家也同样把大面积桑树挖得一棵不剩。L县蚕桑业的悲惨遭遇,只是当时农村经济的一个缩影,也可看作是当年为什么无数的人要逃离家乡,去异地讨生活的一个注脚。“第一代农民工”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且多是由家庭中年龄较小的人率先出去闯荡,有了经验积累后再带动自己的兄长和父辈离开农业,离开家乡……
“印花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本地人不愿做,只有从外地招工。车间里有锅炉,有蒸汽,不管夏天还是冬天,都是光着膀子做事。因为印花是液体印上去的,需要用蒸汽来提高温度,所以车间常年总有四五十度的高温。学徒工150块钱一个月。我先天不足,身体瘦弱,有点受不了。我就给老板写信说:工作太辛苦,条件太差,待遇太低,要求老板改善条件。但是老板不理会。我又煽动员工罢工,大家就不做事了,老板把我找去谈话。这个厂还算可以,没有追究我的责任。
“当时我在跟我的老婆谈恋爱,我把她也带到这个厂里做事。因为丝绸厂要织布,需要女工,她就在那里面织布。我是印花工,她是纺织女工,也是一百多块钱一个月。过了学徒工,印花工后来工资涨到了三百多。说实话,这个工资,相比于农村的收入来说,那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印花的苏州人,工资是我们的两倍。他们也不是好有技术,只是比我们熟练。这是村办企业,集体性质。这个厂不黑,我们的生活条件、住宿水平都还可以,比如素菜是一毛钱一个,油面筋只需要三毛钱一个,吃得舒服。一天下来吃饭只需要几毛钱。一个月十多块钱的生活费。说实话,这次打工还是挺幸福的,就是我的体力太差了。”
在这个印花厂工作的时候,朱建民还把兄长朱七一也叫过去做事,但朱七一是近视眼,戴着一副眼镜,热气动不动就把眼镜蒙住了,做事只能靠手双手来感知。朱七一做了两个月就辞职了。“我哥也真是可怜人,从无锡回来后,把女儿留在家里托亲戚照顾,带着妻子和儿子去新疆种棉花,儿子刚满一岁。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说到这里,朱建民哽咽起来,他抬起手抹着眼泪。
1994年,朱建民因为再次煽动罢工而被开除。在无锡三年间,他与一个本地人交上了朋友,这人虽然大朱建民十多岁,但他们一起谈人生谈理想,成了忘年交。经他介绍,朱建民带着女朋友和一帮老乡,去了另一家印花厂继续当印花工。
“这是一个私营企业,工资给到了500一个月,老板很有钱,那个时候就已经开上了小车。哪晓得干了几个月,老板一分钱不发。我一看形势不好,只有辞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找厂长要工资,他不给。我看到他的豪华办公桌放着一把剪刀——因为剪丝绸需要剪刀,就把剪刀捏在手里,问:你到底结不结账?我把剪刀往桌子上一插,他当即就吓着了,连忙说:结、结、结。对于耍无赖的人来说,你越是低声下气,他就越是不理,只有硬碰硬。这个老板有黑道背景,而我在印花工中是最瘦弱的一个,但我把他给震慑住了。最终,他只把我和我老婆的工资结了,其他人的工资还是没有结。我们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工厂。”
朱建民补充说:这是我打工第二次遇到黑厂。那么第一次呢?我忘记问,朱建民也没有补充。
1996—1998:去新疆“旅行结婚”
离开印花厂后,又去了哪些地方打工,或许还有不少曲折,朱建民都没有讲述。他谈到了婚姻问题。这是1996年。
“我和我老婆谈了三四年的恋爱,但是还没有结婚。——不是准备结婚,而是永远都结不了婚。结婚多少要点彩礼吧,老屋要整理下吧,要买些东西吧,要举行婚礼吧,要过客(宴请亲朋好友)吧,但我没有钱。”
朱家兄弟五人,另有一姐姐早已出嫁。老大是个哑巴,老二是教师,老二结婚后,从大家庭里分开,剩下三兄弟住老屋,老三结婚后,也从老屋搬出,剩下没有结婚的老四和老五一起过日子。
“我为什么跟我家老四感情最深呢?因为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相依为命,吃住在一起,睡一张床,我给他做饭、洗衣服、养猪。我结不了婚,老四也很为我着急,就想了一个计策:让我带着女朋友去新疆。我们把结婚证领了,就去了新疆。其实我老婆家庭条件不错,我的岳父在当地也是一个有名望的人。”
一个女孩子就这样跟着一个空有理想的穷小伙子去了新疆,没有举行任何结婚仪式。这在传统尚未消亡的1990年代中国农村,无论是对于父辈,还是对于子女,都是多么大的一种压力。光舆论的压力,就可把人压垮。
“我们坐七天七夜的火车,去新疆旅行结婚。一路上看到许多地方都是荒无人烟。我们转了几次车,终于到达巴楚县。最后一次转车时,天快黑了,几十公里看不到一个人,一棵树甚至一棵草,清一色的戈壁滩,怪石嶙峋,也担心遇到坏人,我老婆坐上车就哭了。”朱建民转过头对妻子说:“你说你有没有哭?你还记不记得?你哭了。”
朱建民的妻子只在一旁笑。笑声一抽一抽,似乎在努力控制一种想哭的冲动。
“新疆是兵团建设,因为地震多,房子建设得厚,都是一排一排的。总算找到了我哥,在兵团下面的一个小单位——农二连。哪晓得我哥是个豪爽人,两间房子已经住了好几个人,除了我哥一家三口,另外还有他的两个亲戚,都是他叫过来打工的。我哥真讲义气,他自己没有钱不说,一餐还要煮好几个人的饭。我因为新婚,我哥就把他们夫妻住的一间房子让给我们住,他们搬到另外那一间房子,几个人住一间屋。”
在新疆,朱七一一家人第一年承包了39亩棉花地,第二年承包了45亩。朱建民夫妻承包了15亩棉花地。棉花由建设兵团统一播种,他们只需要负责管理。哪晓得种播下去后,第二年春天出了苗,一场大风刮过,棉花苗死光了。新疆初春的风无比凛冽。只好补种。补过的就不一样,因为过了时令,要么减产,要么根本就没有收入。
管理的过程非常艰辛。新疆缺水,得渠道引水,人工灌溉,很需要体力,而且哪里溃堤,得马上补上。朱建民虽然极瘦弱,但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老婆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依然挺着大肚子在地里劳动。在兵团打工的好处是,即使不能赚钱,生活是有保障的。不担心没有饭吃,每个月有定量的小麦供应。“我们更喜欢吃大米,就把小麦卖掉了换大米。那时候我老婆已经怀孕了,需要补充营养,便把小麦背去卖了买羊肉。虽然很穷,但是住房、吃饭都不花钱,生活有保证,搞的是共产主义,所以我觉得还算幸福。这是97年,香港回归,我给我的儿子取名为“润香”——润,是因为新疆本来就缺水,渴望雨水滋润;而“香”就是指香港。润香润香,就是滋润香港。”朱建民妻子临产的时候,是兵团派车送到维族人的医院里,顺产生的,住了三天院,总共花了三四百块。现在家乡人说起“润香”,会说:“哦,就是那个维族人接生的孩子。”
一年下来,补种的棉花不挂果,也就没有收入。种棉花以失败而告终。
“种棉花失败后,我们就去了英吉沙,在那里的农场上开发旱地水稻种植,新疆种植水稻是很稀奇的事情,意思是说如果成功,就能一举成名。搞了几个月,又失败了。”
种地不行,种水稻也不行,他们只好去一个湖北人的建筑工地上做事。30块钱一天。“那时候30的工价,还是很贵的,一个月能挣900块。我和我哥去工地上做事,老婆孩子在家闲着。我们两个人养两家人。我们住在工地旁的一间废弃的泥屋里。因为新疆地震多,这个废弃的屋子到处是裂缝,我们就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在工地上做了不到两个月,接到我二哥的消息——那时候没有电话,我也忘记了是写信还是发电报,反正是说,因为计划生育的问题,让我们一家赶快回去。因为我老婆没有结扎,镇里担心我们生二胎,鞭长莫及,管不了。我二哥是中学教师,如果我们不回来,就会危及他的工作,这就叫做‘株连’。危及到二哥的饭碗,我也心软了,只好辞工。我因为做事很卖力、灵活,老板本想要培养我当架子工,要走的时候,老板很惋惜。据说后来很多人的工资存在扯皮的情况,但是我当时的工资都顺利结给我了。这些钱作为一家人回家的路费。又乘汽车,转火车,再转汽车,回到了家里。”
这是1998年。朱建民一家由于计划生育回到了家里。
“如果当时没有回来,我可能以后还会在新疆奋斗很长时间。有可能干出了一番事业,也有可能一事无成。人的命运,往往是在一夕之间改变的。”
是啊,命运的事情,谁说得清楚呢?命运从来都不曾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1998年下半年,在妻子结扎后,朱建民去浙江打工。出去的时候,他发誓:“没有发财,就不回家。”他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十年。
不是结尾的结尾
2017年腊月底,我碰见了消瘦而健谈的朱建民。
朱建民说:“不努力肯定不成功,但是努力了也不一定成功。一个人成不成功,与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说你生长的环境、社会背景、个人阅历、学历,甚至个人性格都有关系。我之所以不成功,与我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太耿直了。在我打拼的过程中,在我迷茫的时候,始终没有一个人可以指点我。比如我老婆,她一直陪伴着我,但她还不足够指点我。”
问及朱建民妻子对于老公的看法,她依然只是笑,一言不发。
朱七一说:“我老五打工不成功的重要原因还是性格不好,太锋芒毕露了。这与家庭教育的缺失有关,在他几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又过世了。没有人来教导他,一切都得靠自己。”
塆里人说:“建民个性不好,从来不说别人的好话。”
对于个人来说,个性原因导致事业不成功,固然是这样的。但是,在世上还有无数个像朱建民一样努力,一样不成功的人,朱建民不过是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个缩影。追究根本,还是在于他们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将青春献祭给城市,然后等到被时代淘汰,重新回到自己当年出发的地方。如果对比朱建民和朱七一,就会发现,朱建民的心里收藏了很多成功者的故事,他似乎更相信只要通过个人奋斗,就能够发财致富的;但是朱七一认为靠打工并不能提供一条真正的出路,大家必须要抱成团,建设好家乡。
朱建民说,自己过两年就会彻底回家乡,说不定2018年就要回来。“我对我哥的评价,用的是‘伟大’——我用‘伟大’这个词,你不要计较,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伟大的。我哥太不容易,不是一个有钱人,但是这样有号召力。他能把这一帮力量组织起来,把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力量拧成一股绳。”面对兄长所做的事,朱建民感到惭愧,因为自己的经济能力不足,给予兄长的支持太少;自己常年在外,对于大家建设家乡的行动,也没法直接参与。他想着等他回来的那一天,能够贡献出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管理经验和销售经验。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家乡才是唯一的退路,唯一的归宿。就如海子所言:“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
过了2018年的春节,朱建民又要带着妻儿踏上打工之路。他即将48岁了,留给他在外面拼搏的时间当然不多了。他一定常常记起少年时在大山里放牛,面对薄刀锋许下的豪言壮语。薄刀锋形如薄刀,以奇、险著称,仿佛命运的象征。